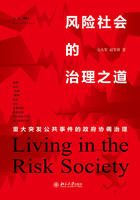
二、治理机制变革不可逆
政府协调的制度变迁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方面因素综合决定的。从制度创新的供给层面上看,政府面对危机治理中公共问题滋生的治理压力,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的高效运作提供了技术支撑,而全球化为全球性公共事件的治理提供了便利等。这些因素累积起来,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供给意愿和能力。从制度创新的需求层面来看,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迫切需要统一的市场环境以及与其相配套的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治理机制;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具体到公共安全领域主要表现为: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滋生的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和区域问题会严重影响我国社会各阶层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公民也迫切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安排解决严重威胁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突发公共事件。因此,尽管仍然存在着某些使制度变迁格局复杂化的因素,但制度变迁的供给和需求因素仍将使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治理机制变革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并不断得以深化。
(一)“倒逼”:突发公共事件的大量涌现
公共危机管理的发展源于危机事件的大量增多。当代世界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所描述的:“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2]我国作为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是各种社会危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时期。据统计,2015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1.9亿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因灾死亡失踪967人,紧急转移安置644.4万人次,因灾直接经济损失2704.1亿元。“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在其中,异常的情况有成为屡见不鲜的情况的危险。”[3]在当下的中国,这种现代性产生的风险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像重金属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PM2.5、危险废物等生态问题集中显现,与之相伴随的是环境上访、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据环境保护部统计,2015年全国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330起,较2014年减少141起,其中重大事件3起、较大事件5起、一般事件322起。其中,环境保护部直接调度处置突发环境事件82起,包括重大事件3起、较大事件3起和一般事件76起。[4]
二是食品安全问题,如苏丹红、地沟油、三聚氰胺、瘦肉精等,数不胜数、触目惊心,公众几乎到了“谈食色变”的程度。“长期以来,我国对食品安全采取的是分段监管模式,即相关政府部门分别负责监管食品供应链上的某一个环节。在实际运行中,各部门、各环节之间往往缺乏良好的沟通和联系,造成初级农产品提供、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消费的完整链条被人为切割,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碎片化,难以形成监管合力。”[5]
此外,我国也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如2015年就发生了西藏日喀则地区地震、云南沧源地震、新疆皮山地震、台风“苏迪罗”和“彩虹”、南方暴雨洪涝风雹灾害等重特大自然灾害。[6]
当前,突发公共事件不断,扩散速度越来越快、处理难度越来越大、破坏程度越来越强。[7]
总之,公共危机管理理论来源于突发公共事件,“脱离事实,任何空洞的论述都会过于简化和歪曲历史”[8]。“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科学只是某种类型的知识,是根据专门方法的准则来获得和证明的知识。”[9]研究突发公共事件时通过剖析典型案例来探究公共危机管理规律尤为重要。
(二)“推动”:社会和市场的发展
公共危机管理发展的动力还来自于社会与市场体制。
第一,社会力量的兴起是政府与企业交换互动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政府和企业的资源、权力、价值不断扩张,而且由于政府与企业“互补论”的推波助澜,逐渐形成了政经一体化的架构。“因而,唯有借助外在于政府和企业的社会力量,特别是成熟的社会组织和普通的社会公众,打破政府和企业持久交换结成的藩篱,才能较为有效地规范政府和企业的交换行为。各自价值目标的实现创造了有利的资源条件及外部环境。”[10]这说明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力量不仅是公共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力量,而且也是规约和引导政府与企业参与、互动的重要因素。社会力量的核心主体是社会组织,一方面社会组织有利于凝聚与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利益维持诉求往往推动应急参与主体在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内采取行动”[11];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有利于引导、动员公众的有序参与、协调合作,降低危机管理的动员成本。同时,社会组织也是政府与公民的沟通桥梁,成为影响政府危机决策的重要因素,并对政府应急管理行为构成了有力的制约,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公共危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市场体制有利于培育多元主体的合作意识。市场体制中,个体通过交易行为,在满足其他个体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实现自身需要的最大满足。市场体制中个人自身需要的最大满足,必须以相互之间的合作为前提。公共危机管理中,对于公民而言,积极参与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尽可能地将自身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而且通过多元协作可以实现自身价值,获得尊重甚至荣誉,提高社会地位。同时,企业是市场体制的主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可以有效壮大多元主体的力量。企业虽然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为使命,但是作为公共危机管理多元主体之一,也必须为与其合作的其他主体承担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以及慈善的责任,而且广泛分布的企业及其产品物流网络可以快捷便利地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提供所需的诸多资源。
(三)“飞跃”:“一案三制”的建立与完善
“一案”是指公共危机管理预案。我国的危机预案框架体系包括六个层次,每个层次的预案体系根据预案的性质和内容对应相应层次的政府协调主体,包括总体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地方应急预案、企事业单位应急预案,以及举办大型会展和文化体育等重大活动的主办单位制定的应急预案。“三制”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制。公共危机管理体制是指公共危机管理的组织结构,包括综合性应急管理机构、专业性应急管理机构、各层级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应急管理机构,以及这些机构所具有的法律地位、权力界限和责任关系。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相较于体制而言,更强调具象性和操作性,是“在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全过程中,各种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应急管理方法与措施”[12]。它是为了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而建立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模式。公共危机管理法制是指已经颁布了的一系列与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有关,从中央到地方应急管理的法律规范体系,这是保证公共危机管理正常履行功能的基本前提。“一案三制”构成了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核心框架,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在制度层面上,中国由防灾减灾阶段直接迈向了综合的应急管理阶段”[13]。政府协调治理体系的构建也是以这个框架为基础展开的。
[1] 同上。
[2]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3]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4] 参见《环保部:2015年全国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330起》,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413/c1001-28274040.html,2018年1月8日访问。
[5] 何莉:《治理之道:推进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载《人民日报》2017年5月8日第7版。
[6] 参见文学国、范正青主编:《中国危机管理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7页。
[7] 2011—2012年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一定影响的公共危机事件有抢盐事件、郭美美事件、“7·23”甬温线动车事故、甘肃正宁校车事故、河南周口“平坟复耕”运动、重庆“8·10”枪击案、贵州毕节流浪儿童垃圾箱闷死事件、河南光山学生被砍伤、“全能神”邪教“世界末日”谣言等。
[8] [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竺乾威、周琪、胡君芳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1页。
[9] 同上书,第1页。
[10] 金太军、袁建军:《政府与企业的交换模式及其演变规律——观察腐败深层机制的微观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1] 贾学琼、高恩新:《应急管理多元参与的动力与协调机制》,载《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1期。
[12] 钟开斌:《风险治理与政府应急管理流程优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13] 童星、张海波:《基于中国问题的灾害管理分析框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