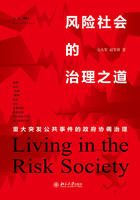
第一章
风险社会危机无处不在
一、政府做好准备了吗
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几乎每一周都有自然灾害和事故灾害等影响公共安全的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以自然灾害为例,仅2013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3.9亿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因灾死亡失踪2284人,紧急转移安置1215.0万人次,农作物受灾面积3135.0万公顷,因灾直接经济损失5808.4亿元。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共启动10次预警响应和39次应急响应,协调派出35个救灾应急工作组赶赴灾区。[1]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们对于公共安全的要求也日益增长。[2]面对突发事件的新态势和公共安全的新要求,政府能否有效应对?政府如何有效应对?这既取决于政府,又不完全取决于政府。为什么?我们先看三个典型案例。
案例一:北京抗击“非典”[3]
2002年的“非典”危机,不但推动了中国的应急管理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转变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观念,改变了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行为策略。
2003年3月6日,北京接报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3月14日,北京第二例输入性“非典”病例患者发病,造成50名医护人员、同机返回人员及其亲属、同期住院人员发病,“非典”开始在北京传播。3月9日,卫生部官员会见了北京市主要医院领导,并通报了疫情,但未向公众公布。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一个全球“非典”警告,但国内媒体未报道。3月26日,新华社报道:北京市卫生局发言人称,北京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病原未向社会扩散。3月31日,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接受采访透露,北京发现12例输入病例,但据后来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已有51例病例。4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非典”防治工作。4月4日,副总理吴仪视察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表示对控制“非典”给予“最高优先权”。4月7日,温家宝总理视察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同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非典”防治工作。4月10日,北京组建防治非典型肺炎卫生防病队。4月17日,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成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任组长。4月20日,中央对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职务作出调整,从这天起,北京加大了对“非典”疫情社会公布的力度,实行疫情每日一报。4月27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强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决定》。北京全面建立“非典”患者的社会救助机制。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撤销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
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会影响甚至破坏社会系统,进而扰乱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而且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例如,2003年“非典”期间的隔离政策,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直到5月22日,北京8万名高三年级学生才可以返校进行考前复习,其他年级的中小学生也是陆续分期、分批、分区域复课。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因受“非典”影响,中国经济总损失额为179亿美元,占中国GDP的1.3%。[4]因此,政府必须积极有效地应对公共危机,将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这是政府应急管理的应然目标,实际情况是否如此?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北京抗击“非典”期间政府的行为和策略。根据前文的案例资料,简单地将北京抗击“非典”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3月6日—4月10日),北京市政府应对“非典”危机的行为是消极的,策略是被动的,可称为“消极被动”模式。例如,思想的不重视导致“非典”的大面积传播,信息的瞒报既贻误最佳的应对时机,又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第二个阶段(4月10日—6月24日),由“消极被动”转变为了“积极主动”,如成立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应对“非典”危机的决定和通知。北京市政府为什么会改变之前的行为模式和策略惯性呢?这可以从4月3日之后中央政府的行为轨迹中看出端倪。中央政府通过“开会”“视察”“讲话”等形式,不断向地方政府和社会传递信号,逐渐形成对于北京市政府的压力,特别是4月20日直接实行政府问责,调整相关负责人的职务,使这一压力达到顶峰,从而彻底改变了北京市政府应对“非典”危机的行为和策略。这说明地方政府(事发地)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行为和策略直接决定了应急管理的绩效;而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行为和策略又受到来自上级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的“压力”影响。“非典”危机中,社会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和公众也有参与,但是处于一种从属或者被动的地位,对于应对“非典”危机的作用和意义有限。因此,政府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毋庸置疑,但是需要注意区分不同层级政府(如事发地政府、中央政府)的属性、角色和关系。抗击“非典”危机的实践表明,政府的行为和策略攸关政府应急管理的效果。
案例二:汶川地震的救援
2008年汶川地震的应急救援中,一方面是政府的高效应对,中央在5月12日晚即决定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全民负责抗震救灾工作,公安部门、卫生部门、地震部门、民政部门、医疗部门、交通通信部门、军队系统、教育部门以及地方政府迅速到位,协调统一接受指挥部领导,共同应对汶川地震。另一方面,社会的参与热情和参与程度让人震惊,截至2009年4月30日,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抗震救灾捐赠款物合计767.12亿元。[5]据不完全统计,汶川地震中总共有来自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200个非政府组织参与援救或灾后重建。[6]但是,由于缺乏救援经验以及缺乏和政府部门的沟通合作,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在救灾前线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境。例如,在地震重灾区茂县,一些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由于手续不全,无法立即参与到前方的救援行动中去。茂县的一位政府官员表示,5月17日接到省里通知,要求所有希望参与茂县救援行动的非政府组织或志愿者,必须事先联系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中国红十字会或四川省慈善总会中的任一部门,通过它们参与救灾工作。然而,他本人也不清楚上述三个部门的联系方式。[7]
与2003年的“非典”危机相比,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汶川地震救援中的行为更加积极,策略更加主动,呈现出积极主动的应对模式。政府及时、公开、透明地发布地震相关信息,满足了社会公众知情的需要,拉近了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距离,如汶川地震的消息在灾害发生后几分钟内就在网络上传播开来。[8]同时积极照顾民众感情、回应社会呼声,如将2008年5月19日至21日设为“全国哀悼日”,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此外,社会的全员参与、政府与社会的协调联动,大大提高了地震救援的绩效。在汶川地震救援中,社会组织和公民呈现出较高的参与性,从人力、财力、物力等各个方面给予政府全方位的支持,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充分说明,社会组织和公民已然成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社会力量是否必然与政府产生“合力”?在汶川地震救援中,社会力量的参与是空前的,政府如何充分有效发挥社会的力量和智慧,实现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构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体系,成为我国应急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汶川地震救援的实践进一步表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影响政府应急管理的绩效。
案例三:广东乌坎事件[9]
2011年9月21日上午,乌坎村400多名村民因土地问题、财务问题、选举问题对村干部不满,到陆丰市政府非正常上访。当日,访民打砸村委会、派出所。9月22日,部分村民组织阻挠、打砸进村维持秩序的民警和警车。汕尾市派出工作组到陆丰督导,陆丰市、东海镇组成工作组进村做工作。9月23日,乌坎村内恢复了正常秩序。11月中旬,工作组正在调查过程中,少数村民在互联网上贴出《“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计划组织村民于11月21日游行上访,并请中外记者报道》的帖子,致使事件出现反复。11月21日,又有400名左右的乌坎村村民聚集到陆丰市政府门口非正常上访,打出“打倒贪官”“还我耕地”等标语。至11月26日,村里的白布标语、大幅宣传画已自行拆除,事态得到平息。12月9日,汕尾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就陆丰市处置“9·21”事件做情况通报。公安部门已经抓获“9·21”事件中打砸为首分子,并继续追捕事件其余犯罪在逃人员,加紧推进取缔非法组织的工作。发布会称“有境外势力对今次事件推波助澜”。12月13日,广东省针对“9·21事件犯罪嫌疑人羁押猝死”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积极做好“9·21”事件犯罪嫌疑人羁押猝死后续工作。12月20日,由中纪委委员、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队的省工作组进驻汕尾陆丰,调查处置乌坎事件,以尽快恢复乌坎法治秩序和社会治理秩序。
前两个案例,政府与社会存在共同的应急管理目标,这构成了两者协调互动、共同合作的基础。这种共同目标会内化为一种心理认同,在抗击“非典”或者地震救援时,心理认同会逐渐转化为信任感和归属感,进而引导社会和公众参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乌坎事件中,政府、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首先,乌坎事件中的政府具有三重维度,一是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基层组织,包括村委会和村党支部[10];二是基层政府,主要是指县(市、区)乡(镇)两级,如陆丰市和东海镇;三是地方政府,主要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地级市)两级,如广东省和汕尾市。其次,政府的三重维度决定了乌坎事件中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三重关系,一是村委会、村党支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二是基层政府(陆丰市和东海镇)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三是地方政府(广东省和汕尾市)与村民之间的关系。这三重关系决定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行为模式,影响政府应急管理的绩效。这也表明,应急管理中的政府协调是多层次性的。
总而言之,三个典型案例中政府无一例外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处于主导地位,这是由政府职能、政府能力和社会结构决定的。首先,从政府职能来看,“处理各种危机或突发性事件,维持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秩序,是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和必备能力”[11],因此,在事件突然爆发时,维护公共安全成为现代国家的首要职责。其次,从政府能力来看,政府掌握着资源分配的主导权,享有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的合法权力,而且层级化、专业化的政府组织体系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是其他应急管理主体所不具备的。最后,从社会结构来看,当前社会结构变动的滞后,以及结构本身还不够开放、不够包容、不够协调的特征,反映出资源、机会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配置还不到位。[12]资源、机会的拥有程度影响应急管理各主体的危机应变能力,从而影响其效用和地位,而权力性质和结构赋予政府系统资源配置的主导权。从我国应急管理的经验来看,无论突发公共事件属于何种类型,政府都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主体。同时,随着我国市场体制的完善和社会的成长发展,社会组织、企业等也日益成长为应急管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因此协调政府间以及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系,“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13],便成为应急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甚或是重中之重。
[1] 参见《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406/20140600654488.shtml,2018年1月8日访问。
[2]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人民对于公共安全的需要也日益提高。
[3] 参见戚建刚、杨晓敏编著:《从灾难中学习——突发事件应对案例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270页。
[4] 参见孙宇挺:《我国因非典损失179亿美元》,载《中国青年报》2003年11月11日。
[5] 参见《民政部公告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款物及使用情况》,http://news.cctv.com/china/20090512/109289.shtml,2018年1月8日访问。
[6] 参见王冬芳:《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机制:公共危机的应对之道》,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7] 参见吴燕:《民间力量的行动与尴尬》,http://www.caijing.com.cn/2008-05-18/100063098.html,2018年1月18日访问。
[8] 汶川地震的消息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公布,分为官方媒体和民间发布两个渠道。一是官方媒体。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14时46分新华网即发出快讯:“12日14时35分左右,北京地区明显感觉到有地震发生”;14点53分,新华网又发出快讯:“四川汶川发生7.6级地震”,随之推出专题“地震应急措施”。二是民间发布。第一个发布发生地震消息的,是百度贴吧的网友——IP为61.161.76.*的百度网友没来得及登录,就在地震吧发出一篇题为“地震了”的帖子,内容简明扼要:“四川地区发生地震。”发帖时间是14时35分,距地震发生时间仅间隔6分钟。参见闵大洪:《汶川地震中互联网传播点滴》,http://news.sina.com.cn/c/2008-05-21/103015586386.shtml,2018年1月8日访问。
[9] 参见庞胡瑞:《广东乌坎事件舆情研究》,载《当代贵州》2012年第2期。
[10] 从法律意义上看,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并非国家权力机关,其中,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属于社会组织的范畴。但是,在行政意义上,无论是村民还是基层政府都将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看作乡镇的下级或是派出机构(参见金太军、施从美:《乡村关系与村民自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225页)。例如,乌坎事件中,村民打出了“惩治贪官”的横幅,这里的“贪官”特指村干部。将村干部当作“官”,说明在村民的眼中,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属于“政府机关”,因此,这里将乌坎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当作政府的“一维”而不是社会的一部分。随着事件的发展,乌坎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属性也在逐渐发生转变,由政府的“一维”转变为社会的一部分。
[11] 金太军:《“非典”危机中的政府职责考量》,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7期。
[12] 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1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