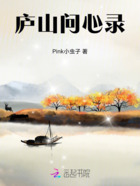
第1章 浔阳归客踏江来
飞机开始下降时,程云修猛然从浅眠中惊醒。舷窗外突如其来的阳光如利剑般刺入瞳孔,他条件反射地抬手遮挡,指节撞到了前排座椅靠背,发出一声闷响。邻座的中年妇女不满地瞥了他一眼,继续低头织那件似乎永远织不完的红色毛衣。毛线针在她粗糙的手指间灵活地穿梭,发出细微的“咔嗒”声,那团红毛线在座椅扶手上微微颤动,像一只被困住的小动物。
“抱歉。”程云修低声道歉,声音因睡眠干涩而沙哑。他揉了揉太阳穴,透过指缝看见云层如破碎的棉絮般散开,露出下方蜿蜒如银练的长江和星罗棋布的湖泊。阳光在水面上跳跃,形成无数细碎的光斑,像是撒落的金箔。水网交织的鄱阳湖平原在五月阳光下泛着翡翠般的光泽,而远处,那片苍翠的山脉如同蛰伏的巨龙——那是庐山,他阔别十年的故乡之山。山顶的云雾缭绕,宛如一条轻盈的白纱巾,那是庐山特有的“瀑布云”奇观。
“各位乘客,我们的飞机即将降落在九江庐山机场,当地气温23摄氏度,天气晴朗...”空乘温柔的播报声在机舱内响起。程云修看了眼腕表,这是一块老式的精工机械表,表盘边缘已经有了几道细小的划痕。下午四点二十分。这趟从LS经停重庆的航班延误了近两小时,让他疲惫不堪。在XZ为期两个月的采访让他晒黑了不少,颧骨处还留着高原阳光灼伤的痕迹,皮肤粗糙得像砂纸一样。他的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些许难以洗净的酥油茶渍,那是他在日喀则偏远牧区采访时留下的印记。
机舱里响起此起彼落的手机开机声。程云修从背包侧袋摸出自己那部老款华为手机,指尖触到采访笔记粗糙的封面——那是他在XZ的成果,关于雪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题报道。笔记本的皮质封面已经磨损,边角处露出了里面的硬纸板。笔记扉页上沾着酥油茶的褐色痕迹,散发着淡淡的松木香,是他在日喀则一家藏餐馆采访时不小心打翻茶碗留下的。那家餐馆的老板娘卓玛当时慌忙用围裙擦拭,却让茶渍渗得更深了。笔记边缘已经卷曲,内页贴满了彩色便签,记录着他在海拔四千米的草原上采访唐卡画师、在风雪中记录格萨尔王史诗传唱的见闻。有一页特别皱,那是他在纳木错湖边写稿时被突如其来的雨淋湿的。
飞机轮子接触跑道时的剧烈震动将他彻底拉回现实。透过舷窗,他看见机场跑道旁“九江庐山机场”六个红色大字,漆面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下方是英文“JIUJIANG LUSHAN AIRPORT”。航站楼造型像展开的书卷,侧面装饰着精美的白鹿浮雕——这显然是近年新建的,他离开九江时机场还在使用老旧的军民两用设施。记忆中的旧航站楼墙上还留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标语,每次经过都让他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新航站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像一块巨大的水晶,倒映着远处庐山的轮廓。
取行李时,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屏幕上“王主编”三个字让程云修条件反射般挺直了腰背。这位《华夏文化》杂志的副主编以雷厉风行著称,手下的记者没少挨训。程云修还记得去年在云南采访时,因为一篇稿子改了七遍还被骂得狗血淋头的经历。
“云修啊,落地了吧?”电话那头传来王主编标志性的大嗓门,背景音里夹杂着编辑部特有的嘈杂声和键盘敲击声,“你那组藏文化保护的报道反响很好,社里决定开个‘传统文化现代传承’系列专题,第一期就做你老家九江。白鹿洞书院、东林寺、浔阳楼,都是文化富矿啊!”王主编说话时总是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把“文化”说成“温化”。
程云修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回应,王主编又连珠炮似地补充:“知道你刚回来辛苦,放你三天假。但下周一我要看到选题方案,要深入挖掘地方特色,体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对了,记得多拍些照片,社里准备做图文专题。”电话干脆利落地挂断了,留下程云修站在行李转盘前苦笑。他太熟悉王主编的风格了——从不给人拒绝的机会,布置任务像发射连珠箭一样密集。
他拖着行李箱走向出口,忽然注意到转盘旁站着一位穿藏袍的老人,正焦急地比划着什么。老人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一样深邃,藏袍的袖口已经磨得发亮。程云修在XZ学了点基础藏语,上前询问才知道老人找不到接机的亲人。他帮老人联系上对方后,老人从怀里掏出一条哈达非要送给他。这条洁白如雪的哈达此刻正安静地躺在他背包的夹层里,散发着淡淡的酥油香气,和他记忆中祖父书架上那本《XZ风物志》里夹着的干枯雪莲花的味道有些相似。
走出机场大厅,五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而下。程云修眯起眼睛,看见停车场里整齐排列的出租车,司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抽烟聊天。香烟的蓝色烟雾在阳光下呈现出半透明的质感,缓缓升腾然后消散。远处,庐山轮廓如黛,山顶还残留着最后一抹冬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戴了一顶银色的王冠。山腰处的云雾缓缓流动,宛如一条游动的白龙。
九江五月的空气带着特有的湿润,混杂着鄱阳湖的水汽、庐山植被的清香,还有远处飘来的淡淡茶香——那是庐山云雾茶特有的兰花香,他童年最熟悉的味道之一。十年前离开时也是这个季节,只是那时的空气里还弥漫着梧桐絮,惹得他鼻炎发作,喷嚏连连。现在街边的梧桐树少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香樟和银杏,空气中少了那种恼人的絮状物。
几个出租车司机操着浓重的九江口音围上来:“老师傅去哪滴?市区走啵?”“到浔阳路只要五十块!”他们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T恤领口处露出金项链的闪光。程云修摆摆手,拖着行李箱走向公交站台。站牌上“机场-市区”的线路图显示会经过长虹大道、浔阳路,终点是烟水亭。这些地名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他记忆的闸门。站台的金属座椅被太阳晒得发烫,他刚坐下又立刻站了起来。
长虹大道旁原来有家“德福居”茶楼,祖父常带他去吃萝卜饼和糯米鸡。那家店的萝卜饼外酥里嫩,咬开金黄酥脆的外皮,里面是清甜的白萝卜丝和鲜香的腊肉丁,每次他都吃得满嘴油光。老板是个胖乎乎的中年人,总爱用沾满面粉的手摸他的头,说“小程老师又带孙子来改善生活啦”。茶楼的八仙桌总是擦得锃亮,上面摆着青花瓷的茶壶,壶嘴处有个小缺口,是某次祖父激动地拍桌子时碰坏的。
浔阳路上曾经遍布古玩店,他总爱溜进去翻看那些泛黄的旧书。有一家叫“汲古斋”的店里,老板收藏了一套民国版的《水浒传》连环画,每次他去都能免费看上一两册。那家店的门槛特别高,小时候他要费很大劲才能跨过去。店里永远弥漫着樟脑丸和旧纸张混合的气味,柜台上的玻璃罐里泡着各种奇怪的药材。后来那条街拆迁时,老板特意把那套书送给了他,现在还在BJ公寓的书架上,书页已经发黄变脆,翻动时会发出轻微的碎裂声。
而烟水亭...那是李白笔下“登高壮观天地间”的地方,也是他和同学们逃课去江边玩耍的老据点。初三那年,他和几个男生在这里偷偷抽烟,被巡逻的警察逮个正着。他们躲在一个废弃的渔船里,却被烟味暴露了位置。祖父来派出所领人时,那失望的眼神他至今难忘。老人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走在前面,背影在路灯下显得格外佝偻。
公交车缓缓驶入城区,窗外的景象却让程云修感到陌生。记忆中的低矮房屋被林立的高楼取代,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狭窄的街道拓宽成了双向六车道,黑色的沥青路面平整得像镜面一样。连曾经热闹的码头区也变得规整冷清,只剩下几艘观光游轮停泊在新建的趸船旁。只有偶尔掠过的老建筑——那座哥特式风格的天主教堂,尖顶上的十字架依然闪耀;那栋民国时期的银行大楼,罗马柱上的雕花依旧精美——还能唤起他的乡愁。
“下一站,四码头,请准备下车的乘客...”机械女声报站打断了程云修的思绪。他看见窗外闪过“信华广场”的巨型LED广告牌,正在播放某款手机的广告。记忆中那里原是一片老式居民区,巷子里有家做豆参煮鱼头的小馆子。老板姓胡,是个退伍军人,左腿有点跛,据说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受的伤。他总爱给常客多添一勺自酿的米酒,那酒装在旧军用水壶里,喝起来有股特别的金属味。程云修十五岁那年第一次喝醉就是在那里,回家吐了一路,被祖父罚抄《醉翁亭记》十遍。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至今还留在他中学的作业本上。
车过龙开河时,程云修注意到河岸砌起了整齐的石栏,花岗岩的表面打磨得十分光滑。两岸建成了步行景观带,铺着红色的塑胶跑道。几株新栽的樱花树已经开过花了,地上还残留着些许粉色的花瓣。他想起高中时这里还是条臭水沟,夏天蚊蝇滋生,居民们都不敢开窗。如今却成了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几个老人正在河边的凉亭里下象棋,棋子落在木棋盘上发出清脆的响声;穿汉服的姑娘举着油纸伞在石桥上拍照,裙摆随风轻轻摆动;年轻母亲推着婴儿车在樱花树下散步,婴儿的小手在空中抓握着阳光。城市变迁的魔力令人唏嘘。
在烟水亭站下车后,程云修沿着滨江路漫步。夕阳将长江染成金红色,波光粼粼的水面像铺了一层碎金。对岸湖北黄梅县的轮廓在暮霭中若隐若现,几艘渔船的黑影在水天交界处缓缓移动。江堤上,三三两两的市民在散步:白发老人打着舒缓的太极拳,动作如行云流水,衣袂飘飘;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不时停下来逗弄孩子,笑声清脆;几个穿校服的中学生追逐打闹,书包在背后一跳一跳,拉链上的挂饰闪闪发亮。远处,一艘货轮拉响汽笛,低沉的声音在江面上回荡,缓缓驶向下游的上海。
他找了一处花岗岩长凳坐下,石面还残留着白天的余温。打开手机备忘录开始构思选题,手机壳上贴着他在LS买的转经筒贴纸,已经有些褪色了。屏幕上的光标闪烁了许久,他却只打出“九江传统文化”几个字。十年记者生涯练就的职业敏感告诉他,这个题目太大太空,需要找到一个独特的切入点。他想起在XZ采访时,那个老唐卡画师说的话:“真正的传统不在博物馆里,而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江风拂过程云修的短发,带来一丝凉意,也带来了远处烤鱼的香气。他抬头望向西边的天空,落日余晖为云层镀上金边,宛如一幅水墨丹青。忽然,他注意到江堤栏杆上刻着的诗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这是白居易《琵琶行》的开篇,当年祖父要求他背诵全文时,他可是叫苦连天。那些诗句现在读来,却有了不同的感受。
琵琶亭就在不远处,新修的仿古建筑在夕阳下熠熠生辉,琉璃瓦反射着橘红色的光芒。程云修记得那里原是一处破旧的凉亭,油漆剥落,木柱上刻满了“到此一游”的字迹。他和同学们常在那里吃冰棍、看江景,把脚悬在栏杆外晃荡。如今修葺一新,成了旅游景点,门口还立着白居易的雕像。雕像前的简介牌上写着:“公元816年,白居易在此送客,写下千古名篇《琵琶行》。”铜像的表面已经被游客摸得发亮,尤其是那只抚琴的手。
程云修走近细看,发现雕像基座上刻着《琵琶行》全文。他的目光停留在最后几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当年背诵时只觉得拗口难记,如今读来却莫名心酸。祖父曾说,读诗要知人论世,四十五岁的白居易被贬江州(今九江),正是在这里写下了这首饱含人生况味的诗篇。那时的江州,对白居易而言就像现在的LS之于程云修——都是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之地,却也因此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天色渐暗,江边的路灯次第亮起,暖黄色的灯光在暮色中显得格外温馨。程云修决定先找地方住下。他打开手机搜索附近的酒店,忽然听到一阵熟悉的旋律——是《春江花月夜》的古筝曲调,从琵琶亭方向传来。循声望去,只见一位穿汉服的少女正在亭中抚琴,周围聚集了不少游客。少女的手指在琴弦上灵活地跳动,指甲上绘着精致的花纹。
琴声如流水,在暮色中格外清越。程云修不自觉地走近,站在人群外围静静聆听。少女弹到“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时,琴音陡然转急,如珠落玉盘。这一刻,他忽然理解了祖父常说的“音乐通神”是什么意思。琴声停止时,周围响起热烈的掌声,有人往琴盒里放钱。程云修摸了摸口袋,发现自己最小的面额是五十元,犹豫了一下还是放了进去。少女惊讶地抬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让他想起纳木错湖水的清澈。
“程云修?真的是你?”
一个清亮的女声从身后传来,带着几分迟疑和惊喜。程云修转身,看见一位穿着淡青色亚麻连衣裙的年轻女子正惊讶地望着他。女子约莫二十七八岁,皮肤白皙,眉眼如画,乌黑的长发松松地挽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颊边,衬得她温婉中带着几分书卷气。她怀里抱着几本厚重的线装书,手腕上一串檀木佛珠随着动作轻轻晃动,散发出淡淡的檀香。她的眼睛在暮色中依然明亮,像是盛着星光。
“许清嘉?”程云修迟疑地叫出这个名字。记忆中那个总爱和他争论古诗释义的语文课代表,与眼前这位气质古典的女子渐渐重合。高中时代的许清嘉总是扎着马尾辫,穿着宽大的校服,眼镜后面是一双充满求知欲的大眼睛。她课桌上永远堆着课外书,从《红楼梦》到《西方美学史》,课间总能看到她埋头阅读的身影。有一次她看书太入迷,上课铃响了都没听见,还是程云修用橡皮砸她才回过神来的。
“天哪,得有十年没见了吧?”许清嘉在他旁边坐下,怀里的书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樟木香,“听说你成了大记者,跑遍全国各地?连高中同学群都很少露面。去年聚会时张老师还问起你呢。”她的声音比记忆中低沉了一些,但依然清脆悦耳,像风铃在微风中轻响。
程云修笑了笑,注意到她左手无名指上没有戒指:“什么大记者,就是个到处跑腿的文字民工。”他指了指自己磨破的背包和沾满灰尘的运动鞋,“刚从XZ回来,那边条件比较艰苦。”鞋面上的灰尘是LS街头特有的红色尘土,怎么拍也拍不干净。
“XZ?”许清嘉眼睛一亮,瞳孔在暮色中扩大,“是去做那个非遗保护的专题吗?我在《华夏文化》上看到你的署名文章了,关于唐卡技艺传承的那篇写得真好。特别是描述老画师用金粉绘制佛像眼睛那段,说那是‘将灵魂注入画布的神圣时刻’,这个比喻太传神了。”她的手指不自觉地模仿着画师的动作,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
程云修有些惊讶:“你还在看《华夏文化》?”
“当然,每期都看。”许清嘉轻轻抚平书页的卷角,这个动作让程云修想起她高中时整理笔记的样子,“我现在在九江学院文学院教书,主讲古典文学。偶尔也帮白鹿洞书院整理古籍。”她拍了拍怀里的线装书,书页发出沙沙的响声,“这不,下周书院要举办‘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国际论坛,我去帮忙做些文献准备工作。”她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没有涂任何指甲油,透着健康的粉红色。
白鹿洞书院?程云修眼睛一亮。这不正是王主编要他做的选题吗?作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南唐,朱熹曾在此讲学并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堪称中国传统教育的活化石。他记得祖父书房里就挂着一幅白鹿洞书院的木刻版画,老人常常对着它出神。
“论坛对外开放吗?我是说,我可以去采访吗?”程云修不自觉地前倾身体,声音里带着记者特有的敏锐。他能闻到许清嘉身上淡淡的墨水香气,混合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茉莉花香。
许清嘉眨了眨眼,睫毛在夕阳下投下细碎的阴影:“当然可以,我还能帮你弄个媒体证。”她忽然笑起来,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怎么,大记者对传统文化感兴趣了?我记得高中时你可是最讨厌文言文的,每次默写《滕王阁序》都要偷看小抄。”她的笑声像一串银铃,在暮色中格外清脆。
“人总会变的。”程云修望向远处的庐山轮廓,暮色中群山如黛,“特别是在XZ看到那些濒临失传的唐卡技艺、格萨尔王史诗后,才发现传统文化就像...”他停顿了一下,寻找合适的比喻,“就像长江水,表面上看不断流逝,实际上一直在滋养着两岸的土地。”江面上,一艘渔船的灯火倒映在水中,被波浪拉长成金色的丝带。
许清嘉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即转为欣赏:“这个比喻很好。其实九江的文化底蕴比你想象的还要深厚。”她如数家珍般说道,手指在空中轻轻比划,“除了白鹿洞书院,还有东林寺的净土宗文化、能仁寺的禅茶一味、周瑜点将台的三国遗迹,更不用说庐山本身——李白、白居易、苏轼、朱熹...多少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足迹。”她的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自豪,眼睛在提到这些名字时闪闪发光。
两人聊起高中同学的近况。班长张毅去了美国硅谷,成了人工智能专家,朋友圈里全是高科技产品的照片;体育委员陈刚继承家里的茶叶生意,现在是有名的“庐山云雾茶”经销商,茶叶罐上印着他的大幅照片;当年总考倒数第一的刘胖子居然考上了公务员,在市政府文化局工作,去年同学聚会时已经胖得认不出来了...
“你还记得教语文的张老师吗?”许清嘉问道,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腕上的佛珠,“他退休后在东林寺旁开了家书院,专门教孩子们诵读经典。去年查出肺癌晚期,却坚持不肯住院,说要在有生之年多教几堂课。”佛珠碰撞发出轻微的声响,像是时间的脚步声。
程云修心头一紧:“张老师...他怎么样了?”他想起那位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老教师。张老师讲课有个习惯,讲到激动处会不自觉地扯自己的领带,以至于那条蓝条纹领带总是歪歪扭扭的。
“上个月走了。”许清嘉声音低了下来,像是怕惊扰了什么,“葬礼上来了好多他教过的学生,大家轮流朗诵《论语》篇章送他最后一程。他临终前说,能一辈子与圣贤书为伴,此生无憾。”她的眼眶微微发红,但很快控制住了情绪。远处江面上,一艘渡轮拉响汽笛,声音悠长而哀伤。
暮色渐浓,江风转凉。程云修想起张老师当年讲解《岳阳楼记》时激情澎湃的样子,粉笔在黑板上敲出一个个白点;想起他因为自己没背出《滕王阁序》而罚抄课文的情景。那些曾经觉得枯燥乏味的古文,如今想来却字字珠玑。他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张老师是在高考结束后的谢师宴上,老人拍着他的肩膀说:“云修啊,你文笔不错,就是太浮躁,要多读经典。”当时他只当是老人的唠叨,现在想来却是金玉良言。
“对了,”许清嘉从包里取出一张烫金请柬,信封上印着白鹿洞书院的徽记,“这是论坛的邀请函,后天上午九点,白鹿洞书院正门。“她犹豫了一下,又补充道,“我可以提前半小时到,带你参观一下书院。这些年修复了不少古迹,还新建了国学体验馆。”她的指尖在请柬上轻轻划过,留下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痕迹。
程云修接过请柬,触感细腻的宣纸上印着书院棂星门的烫金图案,下方是端庄的颜体字:“传承千年文脉,弘扬圣贤之道”。请柬边缘装饰着细小的白鹿纹样,在灯光下若隐若现。他能感觉到许清嘉的手指在交接请柬时微微颤抖,不知是因为江风太凉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谢谢,我一定准时到。”他将请柬小心地放进采访本夹层,忽然想起什么,“对了,你还在研究李商隐的诗吗?高中时你写的《锦瑟》解析可是被张老师当范文全班传阅。”那篇文章他至今记得,许清嘉把“庄生晓梦迷蝴蝶”解释为对现实与虚幻的哲学思考,让张老师赞不绝口。
许清嘉眼睛一亮:“当然!去年还在《文学遗产》上发了篇关于《锦瑟》新解的文章。”她看了看手表,表面在暮色中泛着柔和的蓝光,轻呼一声,“啊,这么晚了!我得赶最后一班回濂溪区的公交。”她匆匆起身,又回头道,“后天见!记得带相机,书院的晨曦很美。还有...”她顿了顿,嘴角浮现出一抹温柔的笑意,“欢迎回家,程云修。”她的背影很快消失在人群中,只有那股淡淡的墨香还留在原地。
程云修在携程上订了信华建国酒店,这是九江老牌的五星级酒店,离烟水亭只有十分钟步行距离。前台小姐用带着九江口音的普通话热情地介绍着酒店设施,还特意给他安排了高层江景房。前台的大理石台面擦得锃亮,倒映着水晶吊灯的光芒。
“先生是来旅游的吗?”前台一边办理入住一边搭话,胸前的名牌显示她姓李,“最近庐山杜鹃花开得正旺,好多摄影爱好者都上山了。”她的指甲涂着淡粉色的指甲油,在键盘上敲击时像十只小蝴蝶在飞舞。
“算是工作吧。”程云修递过身份证,证件边缘已经有些磨损,“我是记者,来做文化专题采访。”他注意到前台电脑旁摆着一盆小小的多肉植物,叶片肥厚饱满,在灯光下呈现出半透明的翠绿色。
“哦!那您一定要去白鹿洞书院看看。”前台眼睛一亮,耳垂上的珍珠耳环随之晃动,“最近在办国际论坛,来了好多外国学者呢。我们酒店还专门推出了‘书院文化主题房’。”她递过来的房卡装在印有书院图案的信封里,散发着淡淡的檀香味。
电梯上升时,程云修透过玻璃幕墙俯瞰九江夜景。长江大桥如一条光带横跨江面,车流在上面缓缓移动,像一串发光的珍珠。远处庐山的轮廓在月光下显得神秘而庄严,山脚下的灯光如同散落的星辰。这座他出生、成长却十年未归的城市,既熟悉又陌生。电梯里的背景音乐是古筝版的《春江花月夜》,与他在琵琶亭听到的是同一首曲子。
房间宽敞明亮,落地窗外是璀璨的九江夜景。程云修冲了个热水澡,温热的水流冲走了旅途的疲惫。他换上舒适的棉T恤,布料柔软得像第二层皮肤。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搜索白鹿洞书院的资料,键盘在他指尖下发出轻微的咔嗒声。网页上的图片唤起了他尘封的记忆——棂星门前那对威严的石狮,朱子亲手栽种的古桂树,碑廊里那些被岁月磨平了棱角的石刻...最难忘的是书院后山那条小溪,他和祖父常在那里野餐,听老人讲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的故事。溪水清澈见底,能看见小鱼在鹅卵石间穿梭。
祖父程砚秋是九江有名的语文老师,痴迷中国古典文化,尤其崇拜朱熹。退休后,他几乎每周都要去白鹿洞书院,有时做义务讲解员,有时只是坐在明伦堂前的石阶上发呆。年幼的程云修常常被迫同行,那时的他对那些晦涩的文言文毫无兴趣,总是趁祖父不注意溜去溪边捉鱼虾,或者爬到树上掏鸟窝。有一次他捉到一只知了,放在祖父正在阅读的《四书章句集注》上,把老人吓了一跳。
直到初二那年,祖父带他去看了书院珍藏的一部宋版《论语》。当老人颤抖的手指轻抚那些历经八百余年依然清晰的文字时,程云修第一次感受到了某种超越时间的震撼。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先贤的智慧穿越时空直抵心灵。那天回家的路上,祖父对他说:“云修啊,庐山不只是风景山,更是人文圣山。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浸透了文化的汁液,每一寸土地都沉淀着先贤的智慧。”老人的眼睛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像是含着泪水。
可惜那时的程云修正沉迷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对祖父的谆谆教诲左耳进右耳出。后来他去BJ上大学,祖父病重时也没能赶回来见最后一面。这个遗憾像一根刺,一直扎在他心里。此刻,窗外的九江灯火通明,而祖父却再也看不到这座城市的变迁了。
电脑屏幕的光在黑暗中显得格外刺眼。程云修关上电脑,走到落地窗前。夜色中的九江灯火辉煌,与记忆中九十年代那个安静的小城判若两地。只有远处庐山的轮廓依旧,沉默地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山脚下的灯光如同一条璀璨的项链,环绕着这座沉睡的巨人。
明天他要去给祖父扫墓,然后好好准备后天的采访。不知为何,他对这次白鹿洞书院之行有种奇怪的预感,仿佛那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采访任务,而是某种等待已久的召唤。窗外,一弯新月悬在庐山之上,清冷的月光洒在江面上,碎成万千银鳞。程云修想起祖父常吟诵的一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今十年漂泊归来,他是否能够看清这座“人文圣山”的真面目?
床头柜上的请柬在月光下泛着微光,棂星门上的白鹿图案似乎眨了眨眼。程云修伸手触碰那个图案,指尖传来微微的凉意。恍惚间,他仿佛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轻语:“回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