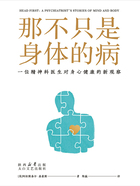
第一章
踏入精神医学的旅途
虽然我和罗兰只有两面之缘,我却清楚地记得他。实际上,在见面前我就听见了他的声音。午饭后,我走回等候室准备开启下午的就诊,忽然一个让人哆嗦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近似咳嗽,又像扑哧的鼻息声。
我和他在诊疗室里坐下来,他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三十三岁,未婚,三年前从加蓬来到英国。从那以后,他觉得喉咙越来越不舒服,导致频繁的爆破般的喷气声。
罗兰在英国的生活很艰难,他努力找工作,举目无亲,女儿和前伴侣在加蓬一起生活,无法和他相见。他的症状起于几年前,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他扑哧扑哧又咳又呛,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我总有种拿块消毒湿巾擦桌子的冲动,专注听他讲话可不容易。朋友们鼓励罗兰去看医生,而他的言外之意是,医生起初并不担心他的症状,后来才把他转介到医院进一步求诊。
我很清楚,罗兰生活中累积的压力和失望加剧了他的神经性抽搐,这种抽搐在他的运动系统里已经深深扎根,乃至进入了自动模式。我见过这样的症状,不寻常的动作和行为经过反复操练后就被固化下来。比如,我见过有些人步态很奇怪,走起路来不自然还费劲,看上去却不像是故意表现出异样,甚至连肌肉和神经都完全没问题。有时候病人会出现顽固的疼痛或眩晕,或者只能轻声说话,生理上却查不出任何毛病,经年累月的医学排查也一无所获。症状有多少种,病人的表现就有多少种。
治疗这样的病人时,即使没有明确的生理原因,我还是会承认他们的痛苦不是伪装或效仿来的,而是和其他任何病症一样真实存在,虽然我们认为这种病症起因于心理层面。
很难了解为什么一个人身上会出现某种特定的症状,比如瘫痪,而不是眩晕和耳鸣。早在20世纪初期就有精神科医生认为人的症状是有象征意义的。比如,一起骇人事件的目击者随后可能会出现失明症状。虽然这种说法仍在精神病学教材里偶尔被提及,但相信这一点的人并不多。
在罗兰的案例里,他的症状起始于咳嗽和喉咙痛,但他对呼吸的持续关注发展成了一种思想负担。堂兄告诉罗兰,他一定是被诅咒了,罗兰觉得日益严重的病症正在应验这个说法。这种担忧只会让症状不断延续,直到咳嗽和鼻子喷气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诸如此类的表现通常被称为“转换障碍”,这个理论认为心理压力会“转换”成生理症状。不过我得承认,目前对这类障碍怎么命名还没有一致的说法。这种分类体系的杂乱反映出多年来我们理解症状的不同方式。有些诊断名称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比如“转换障碍”;另一些诊断则是描述性的,比如“持续性生理症状”,但其实两者讲的是同一件事。“功能障碍”这个术语通常指在身体结构(包括神经、肌肉和器官)完好无损的前提下,身体功能却受损的情况。有时有些术语使用起来还带有贬义或侮辱性,比如,“丧病人”是指打击医生士气的患者,“肥卷宗”用来形容病人厚厚的病历记录。还有一些术语,比如“幕上”(大脑的一个区域),虽然是医学词汇,听上去挺尊重患者,其实却在疯狂暗示病根是在脑子,医生使用这个词就相当于向同行眨眼示意:这病人就该归精神科管。
我拿起罗兰的病历档案,向全科医生口述诊断结果时,有两封信掉了出来。第一封信是耳鼻喉科专家写的,诊断出他的声带有问题。第二封来自神经科医生,诊断他神经系统失调。我开始担心,会不会是我完全误读了他的状况?要不要把我的诊断明确记录在信上?我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自己的判断,因为我知道耳鼻喉科和神经科医生都很精干,对诊断不会马虎的。不仅如此,几周后罗兰来复诊,让我的诊断显得更站不住脚:他竟如释重负,微笑着说症状全部消失了!原来他对我们的“三重奏”医学会诊不抱丝毫信心,就去找了一位同情他的牧师倒苦水,牧师也同意这病一定是诅咒上身,便为他施了圣水。他就这么奇迹般地痊愈了!
我却感觉像被惩戒了一样,非常内疚。罗兰见了四位“医者”,每一位的结论都基于各自对人体或心智的理解,都见到了各自想见到的那部分:耳鼻喉科专家从声带寻因,神经学家沿神经溯源,精神科医师问疾于心病,牧师则施以灵魂的解药。这一切搅动着我的心绪,令我不安,因为我一向以为,我眼中的所见就是事物本来的样子。
这是一种狭窄的视野,医学亦如是,可我们却尽量不去质疑对医学秉持的观念。所有的医学教科书都只教一种呈报病例的公式:首先从流行病学入手,了解疾病有多常见;接着是病因分析和基于医生临床所见的病情陈述;再到病程分析——疾病在没有医学干预的情况下会如何自然发展,最后一步是对疾病结果的预测,即预后。这套程序下,我们讨论的是治疗方案如何干预疾病的自然结果,也就是说,人类必当战胜自然。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里,一直在给医学院的学生上课。他们相信所有的症状都源于疾病,所以应当给予医学检查,再提供一种治疗方案。这个流程在医学训练中被内化成他们的第二天性,以致没有人会去质疑它。隐藏在这背后的信念便是,在这个流程之外的一切东西,都不属于真正的医学。当我试图教学生以另一种方式思考时,他们先是面露一丝怀疑,接着便不安起来。我向他们解释,症状是生命的一部分,大多数时候,疲劳、疼痛、眩晕或背痛并不代表身患任何疾病。好的医生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在医者的角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便是去判断哪些症状需要检查,哪些可以忽略。然而,主流的医学观点和大众舆论不这么认为,症状仍然被视为疾病的表征,依据则是西医实践中普遍采用的“传染病医学模式”。
我们基于这个模式来识别致病原,研发出抗生素或其他药物来攻击致病原,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对传染病的治疗成为现代医学取得的首个重大胜利,循证方法从此开始取代教义和迷信。这种纯科学模式在医学的许多领域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帮助我们了解并医治癌症、心脏病和肾病等诸多疾病。正因为如此,纯科学模式才能成为过去几十年里的不二之选。
然而,只关注治病的科学性却忽略其社会性是一个错误,而今天我们还在延续这个错误。说到底,这种模式不会告诉我们哪些病人会无视症状或怠慢治疗,哪些病人会调整生活来改善预后,也不会告诉我们谁的家属会给予支持,谁会发展出抑郁症乃至想了结生命,而谁又会发掘出不曾自知的韧性。换句话说,只知道如何用科学治病,并不能帮我们了解治疗对一个个体而言是否能够成功。
更糟糕的是,这种科学取向在实际的医疗中造成了无数不必要的检查,最终检查不出什么结果的时候,病人的症状就被当成臆想打发了。有时候,血液化验单或者平扫结果里出现了某个可怕的“偶然发现”,就算和就诊的症状毫不相干,也会引发新一轮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像罗兰这样的病人,症结并不在于症状的真实性——他们的症状是真实发生的——只不过,引发症状的并不是我们在医学教科书里看到的那类病而已。
“健康”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通常不会想太多,而是凭着本能去判断身体好不好。真要思考这个问题,一般也是从“生物学”意义出发,看看我们的器官是不是在各司其职。其实,真正的健康并非仅指身体器官的正常运转,还包括一种受众多因素影响的主观幸福感。人们往往认为密切关注身体有助于长寿或健康,其实这是个谬论,真实情况正相反。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8世纪就敏锐地觉察到,“对健康最致命的莫过于过度呵护它”。我们还没吸取教训,还被鼓动着做更多的筛查项目、健康检查,听从更多提升健康意识的倡议。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前所未有地担心自己的身体,虽然我们从没像现在这样健康过。在富兰克林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马塞尔·普鲁斯特说道:“医生在用药物治好一种紊乱的同时(我听说偶尔能治愈),也给健康的人们接种了致病剂,使得他们出现了十几种其他的紊乱。这个毒性比世界上一切细菌都要强千倍的致病剂,就是‘觉得自己病了’的念头。”
在研究医学史的历史学家眼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斥着“自我”的时代。可穿戴设备监测我们的睡眠、心率和每日步数,却很少有证据证明这样能改善长期的健康状况,(1)(编者注:同此例,全书所有参考文献均见书末汇总)反而会让脆弱群体出现疑病症状——对健康数据的密切关注触发了他们对健康的焦虑,而焦虑则会侵蚀健康的身体。
对健康和幸福的担忧,伤害的并不只有脆弱群体。尽管西方国家的死亡率下降,疾病治愈率上升,我们对健康状况的自我感觉却还不如上一代人。一项调查美国20世纪后半期健康趋势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处在长期还是短期医疗状况下,美国人都比他们的先辈更虚弱、病得更严重。(2)同样在美国,另一项研究发现,人口每增长10%,发生永久性残疾的人数便增长37%。(3)怎么会这样?因病致残的人数怎么会有如此急剧的增长呢?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原因与我们如何看待和思考健康有关。
用背痛来举例,背痛是致残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估计,下背部疼痛在美国每年花费医保系统超过一千亿美元。(4)研究表明,西方国家的下背部疼痛人数增长,这一增长很难用任何背部疾病的发病率来解释。(5)(6)德国的一项研究最有可能给出合理的解释,该研究比较了1990年东德、西德在统一前和统一后十年内的背痛发病率。东德在1990年前的背痛发病率低于西德至少10个百分点,而在接下去的十年间,东德的背痛发病率逐渐“赶上了”西德,等到研究结束,东德的背痛比例已与西德一样高了。研究的作者们对这一现象的成因似乎再无疑问。东德被西德“传染”的不是任何实际的疾病,而是人们对背痛的信念和态度,而这也很有可能是导致美国下背痛发病率激增的原因。(7)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健康?为什么东德和西德对背痛的预期如此不同,使得东德人比他们的邻居西德人感觉更健康?接下去的十年并没有改变东德人的脊背,可他们却开始自觉比过去更痛苦,承受着背痛带来的过度医疗、致残和经济负担。这不是大多数人眼中疾病的样子,也不是我就读医学院时想象中的健康问题。
健康不只是身体无恙,而是一个无形多于有形、精神多于肉体的状态。它也是一种主观感受,不易测量,我们瞬息万变的情绪和预期影响着它。所有这一切并不科学,并不规整,令人沮丧,也是横在医学和心智之间的未知腹地。这是许多医生不愿意踏入的领域,相比之下,做扫描、X光或外科手术来得更干脆,更能给他们带来确定感。
随着人们对身体的科学知识不断积累,医学也变得支离破碎,分裂成太多不同的分支,毕竟这么大的知识体量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掌握的。这样的好处是我们对身体的每一个器官系统都有非常深入的专业理解,患者的某个器官得病了,可以得到高水平的治疗。缺点则是许多医生对他们专业之外的领域不甚了解,只知皮毛。视域不广,则智慧不深。也就是说,医疗提供的是聚焦式的技术手段,因而不太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病人的人格或心理健康状况,而这些因素都会显著地影响症状的表现。可见,把技术取向套用到医学上是场灾难。那些症状与疾病毫无关联的患者因此经历多次医学检查寻找病因,却徒劳而返。就好比开门用错钥匙,虽然拼命转动钥匙,一次比一次更用力,却都是白费力气。这么做不会有任何好处,通常还会造成糟糕的结局,医学也是同理。
对很多病人来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完全没有帮上忙,还让他们在不必要的医学流程里受到了损害。我们把不需要医疗的正常人变成了患者。当这种聚焦于疾病的方法没能套用在有些人身上时,我们就认为是医学的失败,而通常的解决方法却是加大力度地继续套用。这的确是医学的失败,但不是因为我们缺乏理解人体的技术能力,而是因为我们没能理解“人”本身:人们为什么发展出症状?为什么来看医生?我们也常常没能理解病人想从治疗的互动中得到什么。
我们体验到的健康状况和测量到的健康状况之间是脱节的,由此我常想起一个关于心脏病康复的研究(8)。心脏病发作后,一部分心肌细胞凋零了,心脏的工作效率便不如从前。这被称为射血分数,也就是从心室泵出的血量。正常的射血分数值为55%以上,经历过心脏病后这个数值依据受损情况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研究者发现心脏病发作后的致残程度并不总是和射血分数直接相关,而是与病人对疾病的信念有惊人的相关性。如果病人认为患病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们的人生就开始萎缩,停止锻炼和性爱,陷入久坐不动的生活。反之,如果病人认为疾病是可控的,他们就更愿意参加康复训练,从容生活,重拾过去喜欢的工作和活动。决定预后和活动能力的正是他们的信念。心脏病发作后的体力活动是有益身体的(9)。即使心肌受损的程度更严重,情况依然如此。射血分数值为45%的人可以因此丧失活动能力,而射血分数值低到35%的人也可以把人生过得充实而满足。
关于人体,关于它的解剖结构、生理机能、病理分析,我们知道得足够多了。问题在于,情感以种种方式左右着我们对身体的看法和对健康的体验,然而我们——包括医生和病人在内——竟然都很少关注到这一点。
我本人的精神科执业之路是迂回曲折的。我从没打算在大学里学医,却在父母多年劝说下最终申请了医学专业。虽然英国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父母却依旧秉持所谓第二代移民的进步观,觉得当了医生才证明我真正抵达了成功的彼岸。
医学院的面试过程很奇怪。要是面试官问你为什么想学医,一个公认的“自杀式”回答是:“因为我乐于助人。”不管你是不是真心的,这种回答都会被视作肤浅的陈词滥调,所以我知道不能这么说。还记得报考那年只有一个男生在面试时如此作答,回应他的是面试官冷冷的一句:“那你怎么不去学护理呢?”很庆幸我没碰上这个问题,毕竟“是父母逼我学医”这种话也不是什么好答案。
时至今日,如果再有人问我何以对医学感兴趣,我会说:“因为对人感兴趣。”虽然彼时还是医学生的我绝不会把这两者关联起来。那时候,我们关注的是医学的科学性。我们学过人体解剖学,尸体来自向“科学”捐献遗体的人。福尔马林的气味仍能让我回想起上学时的解剖教室,一具具尸体就这样成排摆放在解剖台上。到了第三学期,听到老师让全班“自己去拿条腿来解剖”时,我已全然无感,毫不迟疑地起身,从容踱步至教室后方的大桶摸索出一条人腿来,往回走时只有一个想法,留心手里的腿别砸到了人。
可是,一群十七八岁的青少年对生死、对关乎存在本质的重要议题能有多深的体悟呢?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学生会等到读研时才开启精神病学的训练。医学院教给我们的是如何对人体疾病做出冷静的临床分析,譬如:解剖学揭示五脏六腑的位置,生理学呈现身体如何正常运转,生物化学窥探细胞怎样工作,神经解剖学用于剖析人脑,神经生理学解释正常人脑的运作,病理学研究疾病的规律,还有组织病理学教会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尸体。我们学了如此之多,却一次都未曾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改变与病人的互动,会以无数种微妙而复杂的方式触发病人健康状况的变化。
精神科大夫也都是医生,同心脏科、神经外科还有全科医生一样,都在医学院接受了同样的训练。我们了解身体运作和疾病发生的原理,也知道药物是如何影响人体又被其加工的。然而,精神科大夫还多了一样东西——对人性的理解,这是对人类生活好奇的产物。所思源于所见:我们目睹了人们的个性、智力、遗传和不幸如何以林林总总的方式导致不同的健康状况和疾病。
在取得从医资质后,我的工作压力陡增,得到的支持却微乎其微。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我越把病人视作有待解决的临床问题,而并非带着希望、恐惧和情感的人,生活于我就越容易。我会对同事说:“我去看一下1病房的胆囊,你去瞧一下4病房的痔疮,然后我们再去检查重症监护室那个药物过量。”类似这么讲话的情形并不少见,医生经常不用姓名称呼病人,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可是,在工作头几年的时间里,面对因极度痛苦而过量服药的病人,我的慈悲与好奇慢慢消散。我变得急躁、易怒,开始嫌恶病人给我找麻烦,还剥夺我的睡眠时间。我似乎从没离开过医院半步,深陷糟糕的情绪。那时还是单身的我把原因归结到整天都在工作上,脾气变得愈来愈坏。我在六个月里重了十二斤,毫无疑问,这“归功于”轮班间吃的那些微波炉速食和成包的薯片,外加从护士台拿的巧克力零食。
一个特别的值班夜终于让我意识到这样的状态有多糟。那天是凌晨三点,我从早上八点就开始工作,睡意正酣时,寻呼机突然响了。起初,我晕晕乎乎地以为天亮了,拿起寻呼机才看到是医院总台打来的,说明医院外有人打了电话并且有全科医生接诊了,这意味着接下来的一小时左右急诊室会收治病人,也意味着我睡不成觉了。第二天还要忙碌的我,一想到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整个肩膀都瘫软了。我答复了寻呼机,全科医生说病人是一位疑似心脏病发作的七十六岁老妇,问我能否收治。拒诊自然是不行的,火冒三丈之下我没好气地答应了。
撂下电话后,我知道病人很快就会进急诊室,医院大门隔着值班室的薄墙哐当作响,这让我保持着警觉,时醒时睡。后来我一定又睡着了,因为寻呼机第二次响起时,被吵醒的我再一次脑袋发蒙,随后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寻呼机上的号码并不是从急诊室打来的,不是要告诉我病人已经到了,这是另一个从医院外打来的电话,看来是又收了个病人。我心情沉重地拨了回去,才意识到同我说话的正是之前那位全科医生,他告诉我病人死在了送医的救护车上,不会来急诊室了。一瞬间,我的一夜睡眠,或者说还剩的半个夜晚的睡眠又失而复得了。我喜滋滋地关了灯,躺回医院配发的松垮睡垫,可接下来却睡意全无。我开始心生困扰:一个本可能被我挽救的生命就这样消逝在夜色里,不知道她有没有家人,有没有退休计划,也许还有未竟之事?先前的心满意足很快化为羞耻感——这不是我,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我觉得自己失去了仁爱的本心,而这恰是医者最重要的品质。
在这之后又过了几年,我进入了精神病学领域。就我而言,住院医学的问题是它太容易上手了:那时我已当选为英国皇家医师学会成员,级别仅次于顾问医师,继续往上走看起来是更轻而易举的事。可我感到厌倦了,从医几年后,心脏病发作的病例在我眼里相差无几,接手过的胸部感染、肾衰竭、关节炎和许多其他病例也大同小异。
但药物过量的病人却不同。我会怔怔地听着病人讲述戏剧般的人生,惊惧于人世间的背叛,对人性的脆弱深感同情。而让他们做出悲剧性决定的理由,往往平庸到不值一提,这也让我大感吃惊。我记得有位女病人,因为男友不忠、工作无趣而耿耿于怀,可让她一气之下过量服药的原因,竟是在浴室弯腰捡梳子时不小心把头撞在了水槽底下。谁能想到抬头撞到水槽也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故事吸引了我,让我看到生活的另一面,也揭开了我们生而为人所共有的、最根深蒂固的弱点。
改行成为精神科大夫逾二十五载,我已有能力做生平真正想做的事情,去倾听、去理解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我听过无数人讲述最深的恐惧和未竟的梦想,见过他们对身体病痛的反应、忍受精神疾病的煎熬。我渐渐明白,我们的相似性远大于差异性,我的所见所闻告诉我,人们在面对爱、丧失、救赎、压力和精神疾病进展时的反应,都是人类共通的反应。我们都会陷入恐惧、脆弱和犹疑,但是向自己承认这一点都很难。我们喜欢用一切办法展示力量和自信,从而彰显自己的成功。开什么车、去哪里度假、住什么房子、穿什么衣服、练就什么身材,所有这些都为了证明我们是完美的、重要的。可我们这么做,恰恰是因为缺乏安全感、确定感和自信心。我们渴望通过他人的认可来肯定自己的人生,每个人真正想要的都是相似的东西,那就是:停止内心的自我批判,相信自己是足够好的,知道我们的人生是值得过的。
一个人的人格、态度与信念影响着他在每个人生阶段的生活。回想学生时代,我们身边总有同学无论怎么捣蛋都能逃过老师的法眼,而不那么讨喜的同学做什么都是错。有些孩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取得进步,另一些孩子交个朋友也困难重重。智力中等、天资平平的人能通过勤奋、坚毅和偶尔膨胀的自信,拥有如日中天的事业;而对智力上乘者来说,他们的能言善道在别人听来可能成了咄咄逼人,他们的羞怯寡言可能被视作唐突无礼。如果他们意识不到这点,职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不论是用语言还是非语言交流,我们和外界互动的无数种方式,全都左右着此生前行的方向。
同理,人格也直接影响了我们与身体之间的交流。当身体出现症状,我们是选择无视,还是每次一感觉异样就担心到频繁看医生?我们能不能信赖他人,比如相信医生,还是认为他们的医疗决策背后是大型药企的阴谋,因而选择对医嘱置若罔闻?也许我们会觉得医生出错了,宁愿听从网上看到的建议,或者是深信某个朋友对医生的话反其道而行之的故事。又或许你是那么一个讨人喜欢又执着的人,乃至医生愿意为你付出比其他病人更多的时间来研究新的治疗方案,甚至游说医药公司给你提供某个药物。笃信宗教和文化信仰的人会把病痛理解成一种惩罚;抑郁症会让病人觉得治疗毫无意义,以致不主动求医;而我见过的躁狂症患者则以医者自居来决定自己的治疗,引发悲剧的后果。我们的信念、口才、预期、毅力和精神状态都显著影响着自身的健康状况。然而,作为应该被综合考虑进去的因素,它们的重要性却远未得到重视。
我专攻的精神病学着眼于身体与心理的交叉地带,早年在内科,以及后来在社区和精神科病房的从医生涯让我有经验可循。近二十年里我都受雇于某个精神卫生信托机构,在一家综合医院工作。这是大多数人都很熟悉的一类医院,收治内外科的门诊病人,设有住院病房和手术室。人们因为身体上的健康问题去医院,对求医问诊的预期就是诊断、开方,甚至可能还要考虑手术。很少有人料到就诊结果是去见精神科医师,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由此彻底转变了护理方式。
健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要求我们理解人性、熟悉人体,来达到护理的效果,要面对艰难的决断和未知的因素。这就需要一个人保持灵活,能接纳不确定感。肉体的枯萎原因有限,而生活、经历、人格和心理却能以无穷尽的方式和健康发生关系,并最终呈现在医生面前。这是始终吸引着我的领域。
探索人格和心理如何主宰我们对健康和幸福的体验,是本书的主旨。心理对身体的影响如此之大,可能让你难以置信,却是真实存在的——心理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将成为什么样子。它塑造了我们对症状发生的理解和反应,决定了我们接受怎样的治疗,甚至对疗效亦有影响。
在本章之后的部分,你会看到很多身心问题,来源于多年来我所接诊的案例。从中也许能让你对综合医院精神科医生的工作窥见一斑,也希望本书能帮你打开认识心理、身体和健康的新视角。
(1)Finkelstein, E. A., Haaland, B. A., Bilger, M., Sahasranaman, A., Sloan, R. A., Nang, E. E. K., & Evenson, K.R. (2016). Effectiveness of activity trackers with and without incentives to increase physical activity (TRIPPA):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The Lancet Diabetes&Endocrinology,4(12),983-95.
(2)Verbrugge, L. M. (1984). Longer life but worsening health? Trends in health and mortality of middle-aged and older persons.Th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Health and Society,62(3),475-519.
(3)Colvez, A., & Blanchet, M. (1981). Disabilit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1966-76:Analysis of reported causes.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71(5),464-71.
(4)Katz, J. N. (2006). Lumbar disc disorders and low-back pain: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consequences.The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88(suppl 2), 21-4.
(5)Palmer, K. T., Walsh, K., Bendall, H., Cooper, C., & Coggon, D. (2000). Back pain in Britain: Comparison of two prevalence surveys at an interval of 10 years.BMJ,320(7249),1577-8.
(6)Freburger, J. K., Holmes, G. M., Agans, R. P., Jackman, A. M., Darter, J. D., Wallace, A. S., Castel, L. D., Kalsbeek, W. D., & Carey, T. S. (2009). the rising prevalence of chronic low back pain.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169(3), 251-8.
(7)Raspe, H., Hueppe, A., & Neuhauser, H. (2008). Back pain, a communicable diseas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37(1),69-74.
(8)Petrie, K. J., Weinman, J., Sharpe, N., & Buckley, J. (1996). Role of patients' view of their illness in predicting return to work and functioning after myocardial infarction:longitudinal study.BMJ,312(7040),1191-94.
(9)Ekblom, O., Ek, A., Cider, A., Hambraeus, K., & Borjesson, M. (2018). Increased physical activity post-myocardial infarction is related to reduced mortality:Results from the SWEDEHEART Registr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7(24),e01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