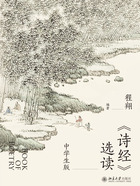
邶风(选12首)
《邶风》,即邶地诗歌,共19首,多数是东周作品。邶(bèi),是周代诸侯国名,在今河南省淇里以北至河北南部一代。周武王灭商,封纣王子武庚于此。《汉书·地理志》记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力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武庚叛乱被杀,邶并入卫。春秋时已无邶国。所以,邶诗皆属卫诗。
【原诗】
柏舟
【注释】
[1]汎(fàn),同“泛”,漂流,浮游。柏舟,柏木做的舟。亦,语助词。一说“亦”为“夜”,也通。流,水流。此句喻指自己无所依托。
[2]耿耿,忧虑不安。寐,入睡。隐忧,忧伤。隐,痛苦。
[3]微,非。以,语助词。敖,同“遨”。敖游,即“遨游”。此句意思是,不是没有酒来遨游消忧,而是忧愁深重,难以消除。
[4]匪,非。鉴,镜子,茹,容纳。此句意为,我的心不是镜子,美丑都接受。
[5]兄弟,指娘家的哥哥和弟弟。据,依靠。
[6]薄言,助词,用于动词前,无实义。一说急急忙忙。愬(sù),同“诉”,告诉。逢,遇。彼,代兄弟。这四句写兄弟不可依靠。
[7]石,磨石。转,转动,移动。
[8]卷,卷起来。这四句写自己意志不可动摇。
[9]威仪,仪容举止。棣棣(dì dì),雍容娴雅。选,挑剔。以上六句写自己内外兼修,无可挑剔,受到不公正待遇,实为冤枉。
[10]悄悄(qiào qiào),忧愁的样子。愠,怒。群小,一群小人。
[11]觏(gòu),遭遇。闵,忧患。侮,欺侮。
[12]静,默默。言,句中助词,无实义。寤(wù),醒来。辟(pì),摽(biào),拍。这两句写内心痛苦难堪,拍胸不止。
[13]居、诸,都是语助词。此句在《邶风·日月》中多次出现。胡,何。迭,更迭。微,晦暗不明。意思是,为何黑暗总是不断。
[14]匪,不。澣衣,即“翰音”,飞鸟之音。《周易·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一说“澣”同“浣”,洗,喻指自己如同没有洗涤过的肮脏衣服。
[15]不能奋飞,不能像鸟那样奋翅飞走。喻指自己不能摆脱忧伤。
【翻译】
水上漂泊柏木舟,河水浩浩任意流。忧虑不安难入睡,内心痛苦有隐忧。不是家中无美酒,也非无处去遨游。
我心不可比铜镜,无论美丑全照入。虽然我有亲弟兄,心灵不通难靠附。我曾去把苦水诉,遭遇弟兄大发怒。
我心不可比磨石,不能随意去转移。我心不可比草席,不能随意来卷起。威仪雍容又娴雅,内外兼修无挑剔。
我心忧愁难消除,总有群小怒火烧。遭遇忧患接连连,受人欺侮真不少。默默反思这遭际,痛苦难堪拍胸号。
太阳月亮照天地,为何黑暗总相依?我心忧伤难消除,好比鸟儿飞不起。默默反思这遭际,笼中鸟儿难展翅。
【导读】
《柏舟》是《诗经》中的名篇。关于这首诗的主旨,《毛诗序》说:“《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郑笺》说:“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君近小人,则贤者见侵害。”孔颖达《毛诗正义》说:“《笺》以仁人不遇,嫌其不得进仕,故言‘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以言‘亦汎其流’,明与小人并列也。言‘不能奋飞’,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传》曰:‘遇者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为不遇也。二章云‘薄言往诉,逢彼之怒’,是君不受己之志也。四章云‘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是贤者见侵害也。”以上三家解说《柏舟》见解一致,即都认为是贤者受小人侵害、不得志之作,这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评价此诗“《柏舟》闷”是相吻合的。另外,司马迁《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郑玄在《诗谱》中写道:“七世至顷侯,当周夷王时,卫国政衰,变《风》始作。”这说明,《柏舟》是卫国政治出现衰败时期的作品,“变”字体现其讽谏作用。
刘向在《列女传·贞顺》作了另外一种解说:
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于卫,至城门而卫君死。保母曰:“可以还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毕,弟立请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愿请同庖。”夫人曰:“唯夫妇同庖。”终不听。卫君使人愬于齐兄弟,齐兄弟皆欲与后君,使人告女,女终不听,乃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穷而不闵,劳辱而不苟,然后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后可以济难矣。《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其左右无贤臣皆顺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贞壹,故举而列之于诗也。
显然,刘向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段将政治诗变成了女子坚守贞操的诗。这是刘向的一种创作,他在《说苑》和《新序》中都运用了这种手法。宋代朱熹《诗集传》在刘向《列女传》的基础上,作了新的解说:“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这个观点影响了后人。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说:“这是一位妇女自伤不得于夫,见侮于众妾的诗,诗中表露了她无可告诉的委屈和忧伤。”这是关于《柏舟》一诗理解上的主要分歧。
哪一种理解更合理呢?《孟子·尽心下》引用了此诗中的句子。一个叫貉稽的人,因为被别人说成是很坏的人,便向孟子倾诉。孟子宽慰他说:“《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孟子认为,孔子和周文王都遭到别人诋毁,并不能伤害他们的美名。可见,孟子把《柏舟》理解为政治诗。《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如下记载:
公曰:“善哉!何谓威仪?”对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周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训以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
显然,这里讲的是为政之道。其实,即便是刘向,他虽然在《列女传》中写了齐侯之女的故事,并不等于他就认定《柏舟》是妇女自伤的诗作,刘向是在用《柏舟》,是一种创作。刘向在其著作中多次引用《柏舟》中诗句,除了《列女传》,还有《说苑·立节》《新序·节士》,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写的一篇著名政论文《条灾异封事》,其中写道:
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
由此可见,刘向是读懂了《柏舟》的,认为它是一首讽谏之作。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驳斥了妇女自伤说,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作了更加精彩的分析,他说:
今观诗词固非妇人语,诚如姚氏际恒所驳……邶既为卫所并,其未亡也,国事必孱。君昏臣聩,佥壬满朝,忠贤受祸,然后日沦于亡而不可救。当此之时,必有贤人君子,目击时事之非,心存危亡之虑,日进忠言而不见用,反遭谗谮。欲居危地而清浊无分,欲适他邦而宗国难舍。忧心如焚,“耿耿不寐”,终夜自思,惟有抚膺自痛。故作为是诗,以写其一腔忠愤,不忍弃君,不能远祸之心。古圣编《诗》,既悯其国之亡,而又不忍臣之终没而不彰,乃序此诗于一国之首,以存忠良于灰烬。亦将使后之读《诗》者知人论世,虽不能尽悉邶事,犹幸此诗之存,可以想见其国未尝无人,所谓寓存亡继绝之心者,此也……呜乎,吾恐邶之忠臣义士,含冤负屈,虽数千年下,犹不能瞑目于九京也!
这段文字写得极有感情,通过想象还原了当时卫国忠臣忧伤国事的情景,读后令人内心无限感伤。由此看来,《柏舟》属于政治诗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非常突出,运用了大量生动新奇的比喻。开头“汎彼柏舟,亦汎其流”的比喻,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入情境之中,夜色之中,茫茫水面上,一只小舟随水飘荡,形象地表达了贤臣遭君抛弃的悲凉之情,使我们想起了那个“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大夫,甚至有学者指出,《离骚》受了《柏舟》的影响。“耿耿不寐,如有隐忧”让我们想到了那个身居茅屋,心忧天下的杜甫。诗中的名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把心与磨石、草席相比,千古少有的比喻,震撼古今,直击心灵,使人联想到历代忠臣良将精忠报国的赤胆忠心。“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心之忧矣,如匪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则形象地揭露了朝廷黑暗、小人横行的乱象,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的那样“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迁客骚人就会“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末两句“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让读者感受到,这位被疏远、遭攻击的贤臣,多么想冲破牢笼,像鸟儿那样一飞冲天!由此看来,这的确是一首政治抒情诗。
本诗共五章,韵脚如下:
第一章“舟”“流”“忧”“游”属“幽”部。第二章“茹”“据”“怒”属“鱼”部,“愬”属“铎”部,“鱼”“铎”通韵。第三章“石”“席”属“铎”部;“转”“卷”“选”属“元”部。第四章“悄”“小”“少”“摽”属“宵”部。第五章“微”“衣”“飞”属“微”部。
【原诗】
绿衣
【注释】
[1]绿,绿色。衣,上衣。黄,黄色。里,衬里。《礼记·玉藻》:“衣正色,裳间色。”黄,正色。绿,间色,杂色。此诗一二句及五六句写绿色为上衣,黄色为里衬、下裳,是颠倒了上衣下裳颜色的礼制,暗示“妾上僭”,乱嫡妾之礼。这是比兴的手法。
[2]忧,思念。曷,何,何时。维,助词。其,代指忧。已,止。
[3]裳(cháng),下衣,像现在的裙。古代服装,上为衣,下为裳。
[4]亡,通“忘”。《小雅·沔水》有“心之忧矣,不可弭忘”。
[5]女,指女妾。一说“女”通“汝”。治,整理,纺织。
[6]古人,前人。一说“古”通“故”,故人,指死去的妻子。俾(bǐ),使。(yóu),过错。
[7]絺(chī),细葛布。绤(xì),粗葛布。二者皆为夏服,现在却用来御寒。凄,凄然。其,助词。以,因为。风,凉风。暗指秋天已到,自己仍穿夏服,感觉寒凉。
[8]实,实在。获我心,合乎心意。获,得。
【翻译】
绿色绿色做上衣,绿色做面黄做里。心啊心啊多忧伤,何时才能来停息?
绿色绿色做上衣,绿色做面黄做裳。心啊心啊多忧伤,何时才能来遗忘?
绿色绿色变名贵,女妾僭越胡乱为。想那前人定礼制,使得人们无是非。
我今仍穿夏时装,秋风吹来送凄凉。想那前人定礼制,着实符合我心肠。
【导读】
当代学者对《绿衣》诗旨主要有两种理解:庄姜伤己和悼亡妻。我们先来看赵逵夫在《先秦诗鉴赏辞典》中对《诗经·绿衣》的翻译:
绿衣裳啊绿衣裳,绿色面子黄里子。心忧伤啊心忧伤,什么时候才能止!
绿衣裳啊绿衣裳,绿色上衣黄下裳。心忧伤啊心忧伤,什么时候才能忘!
绿丝线啊绿丝线,是你亲手来缝制。我思亡故的贤妻,使我平时少过失。
细葛布啊粗葛布,穿上冷风钻衣襟。我思亡故的贤妻,实在体贴我的心。
这与笔者的译文明显不同。赵逵夫说《绿衣》“是一首怀念亡故妻子的诗……自古以来从这方面来表现的悼亡诗很多,但第一首应是《诗经·绿衣》”。持这个观点的还有高亨、余冠英、程俊英、袁梅、向熹、褚斌杰和李山等学者。持庄姜伤己说的有陈子展、袁行霈、方铭、祝秀权、马银琴等学者。
为什么对同一首《绿衣》的理解分歧如此之大呢?古人也有分歧吗?陈子展在《诗经直解》中说:“此诗自来无甚争论。”我们先来看看古人的解说。《毛诗序》说:“《绿衣》,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郑笺》说:“庄姜,庄公夫人,齐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谓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骄。”孔颖达《毛诗正义》和朱熹《诗集传》无异议。
有同学会问,为什么称州吁之母为“妾上僭者”呢?有什么故事吗?这在《左传·隐公三年》有记载: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zhěn,镇定自重)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这段文字记载了州吁之母得宠,庄姜无子,州吁得宠骄纵。这为庄姜自伤说提供了根据。而悼亡妻说则是推测,缺乏根据。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邶风》中,《燕燕》《日月》《终风》《击鼓》以及《卫风·硕人》,多与庄姜、州吁有关,可以看作一组诗。理解《绿衣》应当与其他相关诗作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地理解。
是什么原因让当代学人把“庄姜伤己”理解成“悼亡妻”了呢?张若贤在《多主旨背景下〈诗经·邶风·绿衣〉之“绿衣”解析》[19]一文中认为,悼亡说是由现代学者提出的。首先开始对传统解读有了转折性认识的是闻一多先生的《风诗类钞》:“《绿衣》,感旧也。妇人无过被出,非其夫所愿。他日夫因衣妇旧所制衣,感而思之,遂作此诗。妇人之服,不分衣裳,上下同色,此曰绿衣黄裳,知是男子之服。”闻一多先生结合“女所治兮”,将“绿衣”理解为女子为男子所做的衣服。张若贤进一步分析道:“闻一多先生的这种说法后来延伸到了悼念亡妻说,余冠英、袁唐、王秀梅等多位现代学者支持此说。‘绿衣’是妻子亲手缝制的,如今衣裳尚在,做衣服的人却再也不能相见了。男子睹物怀人,不禁由眼前的‘绿衣’想到妻子的贤惠体贴,斯人已逝,悲伤之感便油然而生。”对古代诗歌,尤其是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诗经》,后人的理解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这是正常现象,是文化消费的需要。我们既不能无视古人观点的合理性,也不能简单否定后人的创新理解,应持有一种包容的胸襟,允许多元理解并存。
陈继揆在《读风臆补》中对“绿兮衣兮”句式作了分析,认为“绿”字“衣”字皆有意义,盖绿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以两“兮”字点缀而丁宁之。这是很有见地的。以此来理解每一章的首句,都能体悟作者的深刻用意。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做了详细分析后说:“此诗但刺庄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词温柔敦厚如此,故曰‘《诗》可以怨’。统观诸说,诗之旨无余蕴矣,定为庄姜作亦无疑矣。”
本诗共四章,韵脚如下:
第一章“里”“已”属“之”部。第二章“裳”“亡”属“阳”部。第三章“丝”“治”“訧”属“之”部。第四章“风”“心”属“侵”部。
【原诗】
燕燕
【注释】
[1]燕燕,即燕子。于,助词。差(cī)池,参差不齐。指双燕翅膀一上一下。羽,翅膀。
[2]之子,这个女子。于归,出嫁。于野,到卫都的郊外。
[3]瞻望,瞩望。弗及,看不见。泣涕如雨,泪如雨下。
[4]颉(xié),向上飞。颃(háng),向下飞。之,语助词。燕子飞翔时上时下,表达留恋之情。
[5]远于将之,即“将之于远”的倒装。之,代词。将,送。
[6]伫立,久立。
[7]下上其音,此句指鸟声随上下飞翔而上下,与前文“颉”“颃”相应。
[8]南,南郊。
[9]实,是,这。劳,思念。
[10]仲,排行老二。仲氏,指所送的女子。任,好。一说信任。只,助词。塞,诚实。渊,深厚。
[11]终,既。温,温和。惠,顺。淑,善良。慎,谨慎。“终……且……”,相当于“既……又……”,如《邶风·北门》有“终窭且贫”。
[12]先君,已故国君。诗人父亲。勖(xù),勉励。寡人,古代国君自称。
【翻译】
燕子燕子飞呀飞,翅膀前后随参差。这个女子要出嫁,送她送到城郊村。举目相望望不见,泪如雨下似倾盆。
燕子燕子飞呀飞,飞到高来飞到低。这个女子要出嫁,送她送到偏远地。举目相望望不见,伤感哭泣良久立。
燕子燕子飞呀飞,上下飞翔声依依。这个女子要出嫁,送她送到南郊去。举目相望望不见,这让我心太忧戚。
二妹是个好姑娘,心灵诚实情深厚。待人温柔又顺和,做事谨慎性敦周。劝我常念先父教,勉励寡人记心头。
【导读】
宋代许(yǐ)在《彦周诗话》中说“‘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真可泣鬼神矣!”明代戴君恩在《读风臆评》中写道:“瞻望追忆之情,千载读之犹为欲泣。”清代陈继揆在《读风臆补》中说:“‘瞻望弗及,伫立以泣’,送别情景,二语尽之,是真可以泣鬼神矣!”可以说,“伫立以泣”四个字所具有的画面感,以及它所引发读者的想象和联想,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清代王士祯在《带经堂诗话》中称赞《燕燕》“宜为万古送别之祖”。清代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写道:“前三章不过送别情景,末章乃追念其贤,愈觉难舍。且以先君相勖,而竟不能长相保,尤为可悲。语意沉痛,不忍卒读。”
后人读此诗大都会被感动。这究竟为什么?
一是因为送别时分产生的伤感之情,乃人类自古就有的一种普遍情感,无论文学是否发达,无论语言文字是否达意,这种情感是客观存在。所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多情自古伤离别”。在周代,我国文学已经十分发达,尤其是抒情短诗的创作早已成熟,正如钱锺书在《谈中国诗》中所说:“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于是诗人就用笔记录下了这难舍难分、依依惜别的时刻,自然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上博简《孔子诗论》载“《燕燕》之情,以其独也”,说的就是这种普遍情感吧。
二是因为《燕燕》一诗的情景交融手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开头两句运用比兴手法,用燕子飞绕久徘徊形象地点染了送别的场景。离人看到飞燕,自然触动情怀,遂诉诸笔端。由燕及人,情酿心中,抑制于胸,适时而发。戴君恩读至“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二句,作眉批道:“不须显言,情自酸楚”,就是这个意思。读这两句,我们想到了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我们想到了《西厢记·长亭送别》中“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钱锺书在《管锥编》分析《燕燕》一诗时,引用了莎士比亚剧作中女子惜夫远行的句子:“极目送之,注视不忍释,虽眼中筋络迸裂无所惜;行人渐远浸小,纤若针矣,微若蠛蠓矣,消失于空濛矣,已矣!回眸而啜泣矣!”可见,中外文学家皆懂得情景交融,只是中国诗人善于点染,虽着墨不多,却风云无限,“含毫渺然”,不似西洋诗人“力透纸背”。
三是文学性提供的空间远大于儒家经典的政治性。《诗经》是儒家经典,重视的是“乐教”“德教”与“诗教”。但客观地说,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文学性。文学性包含教育的作用,但又超越教育性,扩大至更加广阔的人性空间。人性有多大,文学就有多大。读者不必了解诗的具体背景,也不必知道所谓诗旨,凡具常人之情者皆能从诗句中受到触动。明代万时华在《诗经偶笺·序》中说:“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写道:“予谓三百篇正不必作经读,只以读古诗、乐府之法读之,真足陶冶性灵,益人风趣不少。”宋明以来,一些读者越来越能够冲破“经”的藩篱来读《诗经》,发掘其文学价值。
那么,古人是如何解读这首诗的呢?《毛诗序》说:“《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郑笺》进一步说:“庄姜无子,陈女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己子。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孔颖达《毛诗正义》和朱熹《诗集传》也持此说。然郑玄《礼记注》又言“此卫夫人定姜之诗也”,不同于他自己所作的《郑笺》。又据刘向《列女传·母仪传》记载:
卫姑定姜者,卫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妇无子,毕三年之丧,定姜归其妇,自送之,至于野。恩爱哀思,悲心感恸。立而望之,挥泣垂涕。乃赋诗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归泣而望之。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记载了卫夫人定姜送儿媳归娘家的情景,并明确了是《燕燕》一诗的作者。不过,后人对这个记载颇为怀疑,认为刘向是在断章取义,加之刘向编写《列女传》《说苑》《新序》含有创作的因素,难免借用《诗经》之句来为其写作服务。但是,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同学们完全可以站在文学的角度,将《燕燕》作为一首送别诗来理解。
到了宋代,王质在《诗总闻》中认为《燕燕》写的是“兄送其妹出嫁”,打破了“庄姜归妾”说。清代崔述在《读风偶识》中支持王质的说法,他写道:“余按此篇之文,但有惜别之意,绝无感时悲遇之情。而《诗》称‘之子于归’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未闻有称‘大归’为‘于归’者,恐系卫女嫁于南国而其兄送之之诗,绝不类庄姜、戴妫事也。”目前学术界认可王质这种说法。余冠英《诗经选》,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袁行霈等《诗经国风新注》和褚斌杰《诗经全注》都是这个观点。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燕燕》前三章本是民歌,第四章是庄姜创作,然后合在一起。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张剑在《关于〈邶风·燕燕〉的错简》[20]一文中写道,《邶风·雄雉》有“雄雉于飞,泄泄其羽”“雄雉于飞,下上其音”之句,《豳风·东山》有“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之句,《小雅·鸿雁》有“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之句。这说明前三章中的句子为民谣所常见习诵。第四章出现了“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风格上与前三章明显不合,内容上亦无联系。
再说说“差池”这个词。这个词现在经常使用,意思是“差错”。郭沫若《屈原》第二幕有“万一有什么差池,责任是要落在你们的头上”。至于《燕燕》中的意思,则被“参差”替代了。“参差”一词也出自《诗经》,比如《关雎》中有“参差荇菜”之句。部分汉语词汇的含义会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转移,这是正常的。
本诗共四章,韵脚如下:
第一章“飞”“归”属“微”部;“羽”“野”“雨”属“鱼”部。第二章“飞”“归”属“微”部;“颃”“将”属“阳”部;“及”“泣”属“缉”部。第三章“飞”“归”属“微”部;“音”“南”“心”属“侵”部。第四章“渊”“身”“人”属“真”部。
【原诗】
击鼓
【注释】
[1]其镗(tāng),即“镗镗”,击鼓的声音。踊跃,跳跃。用兵,操持兵器。
[2]土国,在都城挖土筑城。城漕,在漕地筑城。漕,地名,在今河南滑县。南行,行军向南。
[3]从,跟从。孙子仲,即公孙文仲,卫国将领。平,联合。陈,陈国,都城在今河南淮阳。宋,宋国,都城在今河南商丘。
[4]不我以归,即“不归我”,不让我回家。以,与。忧心有忡,忧心忡忡。
[5]爰(yuán),于是。居、处,停下,住下。丧,丢失。
[6]于以,于何。之,代词,指马。
[7]契,团聚。阔,离别。古人注“契阔”为勤苦。死生契阔,指聚散离合的动荡生活。子,妻子。一说战友。结合“不我以归”,以“妻子”说为宜。成说,约定。
[8]执,拉,握。偕老,同老。一说回忆当年与妻子相守一生的誓言。
[9]于嗟(xū jiē),感叹词。阔兮,远离,分别。不我活兮,使我活不下去。
[10]洵,久远。不我信,不能让我守信用。
【翻译】
敲击战鼓镗镗响,挥动兵器踊跃上。国都挖漕土筑城,唯独让我奔南方。
跟从将领孙子仲,平定陈宋乱纷争。不能让我回家乡,忧心忡忡难安宁。
在此停留在此住,在此丢失我战马。到哪寻找我战马?树林丛中寻找它。
聚散离合动荡多,想起与妻有誓约。我曾拉着你的手,白头到老决心说。
叹息人生分别阔,这可如何让我活!叹息离家太久远,誓约难守伤心窝!
【导读】
《毛诗序》说:“《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可见这是一首表达卫国人厌恶战争感情的诗。
第一章从大的战场氛围写起,战鼓咚咚,杀声震天,士兵踊跃,挖土筑城,一片紧张气氛。“我独南行”点明心中所怨,因为“南行”意味着远离家乡亲人。第二章写跟从将军出征,并点明出战的地方,使这首诗的内容有了明确指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进一步抒写内心感情。想归而不得,自然忧心忡忡。第三章写南行所到之处,军队驻扎下来,因思家心切,无心备战,纪律松散,战马丢失,只好到树林中寻找。这反映了军士普遍的厌战情绪。无心作战,委婉点明战争的不义性质,不像《秦风·无衣》那样具有“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勇往直前的精神。第四章回忆曾经与妻子立下的誓言,“死生契阔”四字写尽人生离别之苦,动荡生活使多少个家庭不得团圆!这是痛彻心扉的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千古爱情誓言,颇能打动人心。作为回忆之句,表现战士忧虑的是恩爱夫妻何时才能够相见?甚至包含了一种担心在里面。刘毓庆教授在《诗经考评》中分析这首诗时引用了“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是很恰当的。也许这位出征的战士预想到了自己白骨弃野的场景,所以最后一章发出感叹:“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悲伤的感情达到了高潮。
同学们或许要问,州吁是个什么人?我们在《绿衣》一诗中提到此人。他是卫庄公之子,小妾所生。庄公宠爱州吁,使得他飞扬跋扈,狂傲不羁。大臣石碏劝谏庄公,无效。庄公死后,庄公的另一儿子完(戴妫所生)即位,即为桓公。后来州吁杀死桓公,自立为君,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弑君篡位的公子。这在《左传·隐公四年》中有记载。州吁篡位后,联合宋、陈等国连续两次发动伐郑之战,“虐用其民”,使百姓不得安宁,成语“治丝益棼”“众叛亲离”即出于此。《击鼓》一诗当为反映这个时期卫国政局的作品。
本诗共五章,韵脚如下:
第一章“镗”“兵”“行”属“阳”部。第二章“仲”“宋”“忡”属“侵”部。第三章“处”“马”“下”属“鱼”部。第四章“阔”“说”属“月”部;“手”“老”属“幽”部。第五章“阔”“活”属“月”部;“洵”“信”属“真”部。
【原诗】
凯风
【注释】
[1]凯风,南风,和暖的风。棘,酸枣树。心,嫩芽。
[2]夭夭,鲜嫩茁壮。劬(qú)劳,辛劳。
[3]棘薪,酸枣树从幼苗长大。
[4]圣善,聪慧美德。令,好的才德。此句意思是母亲圣明,但自己不成器。
[5]爰,哪里。寒泉,清冽的泉水。浚(jùn),地名,今河南濮阳南。下,地下。
[6]有子七人,生育了七个孩子。
[7]睆(xiàn huǎn),指黄鸟的叫声婉转好听。黄鸟,黄莺。载,语助词。
[8]莫慰母心,意思是作为儿女却不能安慰母亲的心。
【翻译】
南风和乐吹呀吹,吹醒酸枣嫩苗心。酸枣幼苗嫩又壮,母亲养儿太劳辛。
南风和乐吹呀吹,酸枣长大可为薪。母亲聪慧多美德,不肖七子难报亲。
清冽泉水在何处?就在浚邑城下土。养育儿子有七个,母亲生活太辛苦。
黄莺叫声真婉转,声音好好特爽舒。养育儿子有七个,报答母恩无良术。
【导读】
《凯风》本是一首很好懂的诗,也是一首很感人的诗,可是自从《毛诗序》等定调后,使得此诗主旨变得不可思议。
《毛诗序》说:“《凯风》,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此说影响深远。《郑笺》说:“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责之意。”孔颖达《毛诗正义》说:“作《凯风》诗者,美孝子也。当时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夫室,而欲去嫁,故美七子能自尽其孝顺之道,以安慰其母之心,作此诗而成其孝子自责之志也。”宋代朱熹《诗集传》也持此说:“母以淫风流行,不能自守,而诸子自责,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劳苦为词。婉转几谏,不显其亲之恶,可谓孝矣。”
以上四大家都认为《凯风》一诗写母欲改嫁而赞美孝子。这太不可思议!
诗中写道,七子切身感到母亲“劬劳”“劳苦”,称赞母亲“圣善”,便想安慰母亲,这是多么懂事的儿子!母亲自然高兴,欣慰,哪个母亲愿意抛下这样的好儿子,反去改嫁他人?最重要的是,四位大家的解说没有任何证据,恐属臆断。最早解说《凯风》一诗的人是孟子。《孟子·告子下》记载:
(公孙丑)曰:“《凯风》何以不怨?”(孟子)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
这段文字记载孟子回答公孙丑的问题。公孙丑问《凯风》诗中为什么没有怨恨的情绪。孟子回答说,《凯风》中父母的过失小,《小弁》(弁pán)中父母的过失大。做儿女的如果因为父母过失大就疏远父母,是不孝的表现;父母有一点小过失儿女就暴跳如雷,是不应该有的态度(矶,激怒),如果有,也是不孝。孟子讲的是一个基本道理,是教给人们如何把握孝的原则。至于孟子为何说《凯风》中表现的是小过,这个小过是父亲的还是母亲的,还是双亲共有的,孟子没有明说。于是《毛诗序》的作者进行了想象发挥,歪曲了母亲形象,以至于想象这位生育了七子的母亲受淫风影响想要改嫁。
对于《毛诗序》,向来有首序和续序之分的说法。如将二者分开,说“《凯风》,美孝子也”,勉强说得通。但是续序若在无本事可征的情况下出此断语,就属杜撰了。陈卫南在《孝心可鉴垂后世,母氏圣善谁人知?——〈诗经·凯风〉赏析》[21]一文中说:“《诗序》一派,唐突玷污圣善伟大的七子之母,致使《凯风》蒙耻含诟,坏其名声达三千多年。”
对四大家的观点,后人不是没有质疑者。比如明代季明德就说过“要是杜撰”。清代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写道:“况诗中本无淫词,言外亦无淫意,读之者方且悱恻沁心,叹为纯孝感人,更何必诬人母过,致伤子心?”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写道:“对于表现骨肉至情的作品,朴素的语言常是最理想的语言,平直的手法常是最成功的手法,往往能取得最强烈的艺术效果。”《凯风》就是这样一首语言朴实无华的诗作。褚斌杰在《诗经全注》中说:“这是一首感念母爱的诗。”笔者非常赞同。解文超、马刚在《〈诗经·凯风〉主题及意象研究》[22]一文中说:“《凯风》的基本主旨是歌颂母亲的崇高美德,兼及歌颂孝子,故《孔疏》《朱传》以及后来治《毛诗》者持此‘卫之淫风流行’及‘怨母、谏父’之说失当。”
传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并作《南风歌》云:“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尔雅·释天》云:“南风谓之凯风。”邢昺疏曰:“南风长养万物,万物喜乐,故曰凯风。”凯者,乐也。在《凯风》一诗中,“凯风”意象的含义是清晰的。“棘心”和“棘薪”的含义也是清晰的,比喻七子成长的过程。母亲含辛茹苦,艰苦备尝,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寒泉”滋润大地,其养育之喻也不含混。至于“睆黄鸟”的“好音”,则是用来反衬七子不能报答母恩自愧之情的。诗中除了写七子自责外看不出还有什么孝行。所以说,此诗主旨并非什么“美孝子”,而是一首歌颂母爱的诗作。感念母恩,无以为报,所以自责,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后世文人常用“凯风”一词表达母爱,此类诗文颇多。古乐府《长歌行》有“凯风吹长棘,夭夭枝叶倾。黄鸟飞相追,咬咬弄音声。伫立望西河,泣下沾罗缨”。苏轼在《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词》一诗中写道:“回首悲凉便陈迹,凯风吹尽棘成薪。”朱熹晚年改变了自己的观点,用“凯风寒泉之思”比附自己的母亲。
本诗共四章,韵脚如下:
第一章“南”“心”属“侵”部;“夭”“劳”属“宵”部。第二章“薪”“人”属“真”部。第三章“下”“苦”属“鱼”部。第四章“音”“心”属“侵”部。
【原诗】
谷风
【注释】
[1]习习,风连续不断地吹。谷风,山谷的风,大风。以阴以雨,阴天下雨。以,是。此两句喻指丈夫暴怒态度。
[2]黾(mǐn)勉,勤勉,努力。同心,两人同心相爱。宜,应当。
[3]采,采用……为菜。葑(fēng),芜菁。菲(fěi),萝卜。以,用。下体,根茎。葑、菲的根茎与叶皆可食用,根茎是主要食材,叶过时即不可食用。根茎比喻女子之德,叶比喻女子美色;女子虽然色衰,但仍有美德,丈夫却嫌弃妻子。此二句谴责丈夫重色轻德。
[4]德音,美好动听的话。《诗经》中“德音”出现多次,含义不同。莫违,不要违背。及尔同死,与你白头到老。这是当初男子说的“德音”。
[5]行(háng)道,道路。迟迟,行走缓慢。中心,内心。违,怨恨。此二句写女子被逐出夫家。
[6]不远,不肯远送。伊,是。迩,近。薄,勉强。一说语助词。畿,门槛。此二句写丈夫不肯远送,仅送至门口。
[7]荼(tú),苦菜,味苦。荠(jì),甜菜。此二句写苦菜虽苦,但比起被弃后内心之苦简直如甜菜。反衬手法。
[8]宴,快乐。昏,婚。此二句写丈夫与新婚妻子快乐情景,与自己被弃形成鲜明对比,谴责其丈夫喜新厌旧。以兄弟称婚姻,颇见于先秦两汉古籍。参见袁行霈等《诗经国风新注·邶风·谷风》“析疑”部分。
[9]泾,泾河。以,因为。渭,渭河。浊,浑浊。据史念海《论泾渭清浊的变迁》[23]考证,春秋前泾水清于渭水。湜湜(shì shì),水清。沚,水底。弃妇以泾水自比,丈夫却清浊颠倒,但弃妇相信自己心地是清纯的。各版本对此二句的解读多有不同,本书为其中一种。
[10]不我屑以,即“不屑于我”。不愿与我为偶。
[11]毋,不要。逝,到,往。梁,拦水捕鱼的石堰。发,打开。笱(gǒu),捕鱼的竹篓。此二句意思是警告新妇不要动我的东西。
[12]躬,自己。阅,容纳。遑,闲暇。恤,顾念。后,走后。此二句意思是自己走后顾不上很多事情。
[13]就,遇到。深,深水。方,竹筏。这里作动词,乘竹筏渡河。之,语助词。
[14]浅,浅水。泳,潜水。以上四句比喻自己料理家务能力强,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能处理好。
[15]何有何亡,偏指无。亡,无。黾勉,努力。求,做好。此二句写于夫家时尽力做事。
[16]民,指邻人。丧,凶事。匍匐,全力。救,帮助。此二句写帮助邻里。
[17]慉(xù),喜爱。不我能慉,即“不能慉我”。雠(chóu),同“仇”。
[18]阻,拒绝。德,善心。贾(gǔ)用,卖东西。不售,卖不出去。
[19]昔,昔日。育,生活。恐,担心。鞫(jū),贫困。及尔,同你。颠覆,患难。此二句写当初与丈夫共患难。
[20]既,已经。生、育,指生活好起来了。一说生儿育女。比予于毒,把我比作毒物。予,我。于,如同。
[21]旨蓄,积攒起来的美味。御冬,过冬。御,抵御,防备。
[22]御穷,抵御贫穷。此四句说自己成就了你们的好生活。
[23]有洸(guāng)有溃,水大奔涌而出,四处奔泻。比喻丈夫怒火肆虐。诒(yí),留给。肄(yì),劳苦。
[24]伊,惟,只。来,语助词。塈(kài),怒。此字读音及解释有分歧,本书用王引之说。
【翻译】
山谷大风习习吹,好似阴天雨纷纷。努力与你心相爱,不应对把我怒喷。芜菁萝卜重根茎,你却喜欢绿叶新。当初你曾对我说,白头到老永相亲。
路上行走步缓迟,怨恨悠悠满胸臆。薄情寡义不远送,勉强送我到门里。谁说苦菜味难忍,若比我心是甜荠。你又新婚多快乐,两人亲昵如兄弟。
泾水清清渭染浊,我心清清不可夺。你又新婚多快乐,不愿与我成伴伙。不要到我石堰去,我的鱼篓不许摸。我身尚且不受纳,哪有闲暇顾太多。
如果河流水太深,就乘竹筏小舟过。如果河流水太浅,潜水游过不耽搁。家里如果缺什么,我就勤勉做好活。街坊邻居有丧事,全力帮助赞誉多。
非但不想喜欢我,反把我当仇敌跺。拒绝我的好心意,如同商贾难卖货。往昔担心穷困多,与你共患来度过。生活渐渐好起来,你就视我如毒货。
我把美味攒起来,抵御冬天防难过。你却新婚图快乐,用我抵御穷生活。怒气奔涌来发泄,给我留下苦难多。从不顾念往昔情,只用愤怒对待我。
【导读】
同学们在高中语文课本中学过《氓》,写一个女子婚姻的不幸。这首《谷风》与《氓》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
两首诗都采用女子视角来叙事,都采用回忆的倒叙手法,都于叙事中带有浓厚的抒情成分。《氓》对女子婚前的内容写的比较多,比如写男子“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也写了婚前女子对氓的迷恋,“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涕泣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可以说,从恋爱写起,写到结婚,写到婚后生活,最后写到决绝,故事的完整性强。而《谷风》则不同,对婚前的情况几乎没有介绍,只有一句“德音莫违,及尔同死”。为什么这样写呢?朱熹《诗集传》说:“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怨之情。”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本诗重点写婚后被弃的内容,“德音”是用来表现男子背弃誓言的品行,与婚后不念旧情寻找新欢形成对比。至于婚前男子如何发誓,如何用动听的话来骗取女子的芳心,只有靠读者借助想象来弥补了。能不能用《氓》中婚前的内容来填补《谷风》空缺的内容呢?不妥。因为《谷风》中多次出现“宴尔新昏”一句,它使读者想象,很可能是“我”与新娘子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以至于有了“无逝我梁,无发我笱”这样的诗句。这应当是两首诗的明显不同。当然,两个女子都很单纯,轻易相信了男子的甜言蜜语。这大概是一些青年女子的弱点,这也是人性的弱点。还有一点相同,就是两个男子都背叛了爱情,背叛了誓言。也许当初男子的感情是真挚的,后来却变了,给女方造成了深深的伤害。这种悲剧,从古到今一直上演,而且还会演下去。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氓》中女子对自己的经历作了深刻反思,向其他青年女子提出了忠告:“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是切身的教训,痛彻心扉。不同的是《谷风》中的女子没有发出这样的警告,她更多地在叙述自己在家庭中的不幸遭遇,在倾诉自己内心的苦楚。“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行道迟迟,中心有违”,“宴尔新昏,如兄如弟”。这是责备丈夫的喜新厌旧,就是说,她被丈夫逐出家门了,是个弃妇。她甚至还在埋怨丈夫送她时连门都不出,“不远伊迩,薄送我畿”。她于是发出“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她一再说明自己对家庭是如何全力付出,“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读这些句子,读者心中会感到凄楚,同时也感到这是一个性格懦弱的女子,不敢反抗,不敢斗争,更没有决绝的勇气,这可能与她生育了孩子有关。她用“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来比喻自己内心的高洁,是很感人的,这个女子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她怨恨丈夫“不念昔者,伊余来塈”,似乎对丈夫回心转意抱有一丝希望。这样的心理刻画是细腻的,也是真实的,她对丈夫的爱没有泯灭,但丈夫对她已经厌弃了。这种爱的差别是本诗的一大特点。正因为如此,读者才对她产生了极大的怜悯,并谴责她丈夫的背叛行为。
我们还看到,《谷风》中的女子乐于助人,对街坊邻里的事情热情相助。“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这两句话很感人,它让读者扩大想象和联想——这是统治者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感!方玉润的“逐臣自伤也”的观点正是从这个角度产生的。但是,即便如此善良,这个女子仍然被丈夫抛弃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告诉我们,她的丈夫嫌她不再美丽了,“宴尔新昏”了,“夫妇失道”了。而在《氓》中,女子对家务也是全力操持,但是只限于家庭内部,没有与街坊邻居的交往。我们也看不到氓喜新厌旧,移情别恋,看到的是氓“二三其德”以及“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家暴行为。
《氓》中女子不是被逐出家门的,是她自己主动提出离开的,“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女子不愿意继续过备受煎熬的生活,最后发出“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决绝之声。读者看到了一个性格刚烈的女子。《谷风》中的女子,心怀怨恨,虽被抛弃,却恋恋不舍,“黾勉同心,不宜有怒”“行道迟迟,中心有违”。她如泣如诉,怨而不怒,情感更加复杂,难以与家庭一刀两断,可能这个女子还有自己的孩子。两首诗写了两位女子,性格迥然有别,都很生动,都很感人。《诗经》把笔触深入到女子的悲剧命运中,表现出深深的悲悯情怀。这就是《诗经》现实主义的诗风,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作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往往有其“诗教”功能。《毛诗序》说:“《谷风》,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这样的“诗教”是有其积极作用的。《谷风》突出了“女德”,再联系《关雎》提倡的“君子配淑女”的婚姻模式,我们对儒家关于“夫妇乃人伦之始”观点的或许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本诗共六章,韵脚如下:
第一章“风”“心”属“侵”部,“雨”“怒”属“鱼”部,“菲”“违”属“微”部,“体”“死”属“脂”部。第二章“违”“畿”属“微”部,“荠”“弟”属“脂”部。第三章“沚”“以”属“之”部,“笱”“后”属“侯”部。第四章“舟”“游”“求”“救”属“幽”部。第五章“雠”“售”属“幽”部,“鞫”“霞”“育”“毒”属“觉”部。第六章“冬”“穷”属“侵”部;“溃”“塈”属“物”部,“肄”属“质”部,“物”“质”合韵。
【原诗】
式微
【注释】
[1]式,发语词,无实义。微,幽暗;又解为微贱、衰败。“微君之故”和“微君之躬”的“微”是“如果不是”的意思,表示假设。
[2]胡,何,什么。归,回家。
[3]君,你。一说黎侯。课文注释为“奴隶主”。故,缘故。胡为,为什么。乎,在。中露,即“露中”,比喻生活在艰难之中。
[4]躬,身。泥中,比喻生活在艰难之中。
【翻译】
天色渐渐暗下来,为何不见把家还?如果不为君之故,何必遭受露中苦?
天色渐渐暗下来,为何不见把家还?如果不为君之身,何必忍受泥水侵?
【导读】
对《式微》的解说,自古分歧很大。《毛诗序》说:“《式微》,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据《左传》记载,周宣王十五年,晋国灭黎侯国,随即又复其国。周惠王十四年,潞子国灭黎侯国。周定王十三年,晋国灭潞子国,又将逃在异乡的黎侯后裔请回,重建黎侯国,不久晋国又灭之。由此推测,《毛诗序》对《式微》的解说是有依据的。袁行霈等《诗经国风新注》中持此说。
再一种解说依据的是刘向《列女传·卷四·贞顺传》,内容如下:
黎庄夫人者,卫侯之女,黎庄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务者异,未尝得见,甚不得意。其傅母闵夫人贤,公反不纳,怜其失意,又恐其已见遣而不以时去,谓夫人曰:“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诗曰:“式微式微,胡不归?”夫人曰:“妇人之道,壹而已矣。彼虽不吾以,吾何可以离于妇道乎?”乃作诗曰:“微君之故,胡为乎中路?(路通露)”终执贞壹,不违妇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编《诗》。
这个故事比较完整,具体展现了《式微》成诗的过程。如果按照这样的背景来理解《式微》,那么这首诗显然是一首形式别致的对唱诗,可以重新标点如下:
(问句)“式微,式微,胡不归?”(答句)“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问句)“式微,式微,胡不归?”(答句)“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前问后答,有问有答,答句采用反问,答案包含问中。这种对唱形式在《诗经》中虽非孤例,但并不多见。李山先生在《诗经析读》中持此说。
还有第三种解说,是男女感情说。这又具体分为三种观点:或解为妇人遭辱呼告丈夫,或解为女子被弃呼唤情人,或解为情人幽会。(参见《诗经学大辞典·三百篇解题卷·式微》),但缺少有力的文献依据,恐属附会。
中学语文课本与以上诸种解说都不相同,可视为第四种解说。课本说解说如下:
这是一首劳役者的悲歌,以咏叹的方式、质问的语气,直抒胸臆,堪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经典之作。
课本之所以这样解说,是受了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还有余冠英的《诗经选》、袁梅的《诗经译注》(国风部分)等。我以为语文课本最好不选此诗。若要选表现反抗压迫的诗作,不妨让《硕鼠》重回教材。《硕鼠》运用拟人手法,读来朗朗上口,自古及今理解上的分歧不大。
综合以上各家观点,臣劝君归之说较为可信。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公欲无入,荣成伯赋《式微》,乃归。”这是发生在公元前544年的故事。由于宋国大兵压境,鲁襄公便逃往楚国,不敢返回。但国不可一日无君,大夫荣成伯力劝襄公回国,并吟诵了《式微》,终于使鲁襄公回到鲁国。这实在是重演了黎国臣子劝黎侯归国那一幕。这个故事距离《式微》最近。
正因如此,所以《式微》这首诗对后世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突出表现在“式微”和“胡不归”的词句上。后世文人常用“式微”来表达归隐、微贱、衰弱之意,如王维《渭川田家》有“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之句,孟浩然《都下送辛大夫之鄂》有“因君故乡去,遥寄《式微》吟”之句;另外,崔璞有“作牧惭为政,思乡念《式微》”之句,贯休有“东风来兮歌《式微》,深云道人召来归”之句。至于“胡不归”的影响,则见于楚辞《招魂》《招隐士》中“归来兮”“魂兮归来”“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还有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顾况《游子吟》中“胡为不归欤,辜负匣中琴”。王维《山中送别》中“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
评价一首诗好不好,固然应该顾及全诗,但是若有一二名句名词流传后世,令人爱不绝口,那也应该是好诗的标志吧?《诗经》中这样的诗作很多,很多。
本诗共二章,韵脚如下:
第一章问句“微”“归”属“微”部,答句“故”“露”属“鱼”部和“铎”部,“鱼”“铎”通韵。第二章问句“微”“归”属“微”部,答句“躬”“中”属“侵”部。
【原诗】
简兮
【注释】
[1]简,鼓声。《商颂·那》:“奏鼓简简。”
[2]方将,正要。万舞,古代大型舞蹈,包括文、武两部分,舞者或手持兵器,或手持鸟羽,或手持乐器,规模宏大,场面壮阔。万,大。《商颂·那》有“万舞有奕”,《鲁颂·宫》也有“万舞洋洋”。
[3]日之方中,正午时分。
[4]在前上处,指领舞的位置,在最前方。
[5]硕人,身材高大的人,指领舞的舞师。俣俣(yǔ yǔ),魁梧。
[6]公庭,庙堂的前庭。
[7]执,手持。辔(pèi),马缰绳。组,丝带。
[8]籥(yuè),乐器。有孔,像笛子,舞者边吹边舞。
[9]秉,执,拿。翟(dí),雉鸡尾部的羽毛。
[10]赫,面部红而有光泽。渥(wò),涂抹。赭(zhě),红土。
[11]公,指卫国国君。锡(cì),通“赐”。爵,本指酒器,这里是赏赐的酒。
[12]榛(zhēn),树名,结的果实像栗子而小。
[13]隰(xí),低湿的地方。苓,甘草。
[14]云,语助词。谁之思,即“思谁”的倒装。
[15]西方,指周室。周在卫国西边。美人,指舞师,可能是从周室来的专业舞蹈家。
【翻译】
鼓声简简响起来,万舞将要舞起来。太阳正对他头顶,站在舞者最前排。身材高大特魁梧,君庙前庭舞起来。
看他力大如猛虎,手持马缰如丝巾。左手握着乐器籥,右手拿着雉鸡锦。面色红润如涂赭,君王赐他美酒饮。
山上榛树郁森森,低处甘草绿茵茵。问我心中思念谁?来自西方那美人。只是那个美人啊,他是西方来的人。
【导读】
“万舞”究竟是什么舞?因为有了《简兮》我们才略知一二,作为文献资料,十分珍贵。据说,万舞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了,甚至有人说夏代就已存在。传说中的更古老的“云门舞”只有其名,不知其实,因此,说万舞是目前尚且知道内容的中国最古老的舞蹈应该没有问题。
从《简兮》的记载可以看出,万舞是在郑国宗庙庭前演出的。演出之前,观众就已经听见咚咚的鼓声了,“方将万舞”四个字渲染了气氛,观者屏气凝神,静静等待着舞蹈的正式开始。到了正午时分,演出开始了。“日之方中”应该是规定好的演出时间,大概正午这个时间与万舞正相匹配,其他时间则不适宜。舞蹈队伍人数众多,站在最前排的是领舞者。这个人长什么样呢?高大魁梧,他带领众人演出万舞,这个人应该是万舞的灵魂级人物。
读到这里,我们猜想,一定有一双眼睛,——不,应该是很多双眼睛紧盯着领舞者,他的高大形象占据了观众的心。接下来,第二、三章集中写领舞者。他孔武有力,像猛虎一般。褚斌杰《诗经全注》认为,舞师是由西周王室来的,美人就是那位硕人舞师。舞者先是演出武舞,做着骑马奔驰的动作,马缰绳在他手中如同丝巾一样柔软。然后是文舞,舞者左手持乐器,边舞边吹,音乐美妙动听;右手拿着雉鸡的羽毛,上下翻飞,左右翩跹。舞者脸上红润生光,好像涂了一层赭土做的颜料。舞者演得太好了,国君赏赐了美酒。
有人说“山有榛”比喻男子,“隰有苓”比喻女子。所以,接下来写女子对男子的思慕。这样好的男舞者,怎能不让观看的女子心生爱慕呢?下面以一个女子的口吻写道,若问我心中想念谁,就是那个西方的美男子啊!可是,那个美男子来自西方周室,大概不会在郑国久留,我的思念不会变成现实。这样理解美不美呢?当然美。甚至我们可以再扩大一点,观众在演出结束后,还依依不舍,边走边议论着,各自说着自己心中喜欢的演员。这里的观众,既可以是女子,也可以是男子,既可以是青年,也可以是老年,思慕已经不限于男女之间了。
古人是怎么理解这首诗的呢?《毛诗序》说:“《简兮》,刺不用贤也。卫之贤者仕于泠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泠官,就是伶官,就是同学们学过的欧阳修《伶官传序》中的伶官。《毛诗正义》写道:“作《简兮》诗者,刺不能用贤也。卫之贤者仕于伶官之贱职,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为王臣,故刺之。”并将“西方美人”定为西周贤者,将“硕人”定为宜举荐重用之人。朱熹《诗集传》则认为“贤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轻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誉而实自嘲也”,遂开“玩世不恭”之说。朱熹还进一步指出:“‘西方美人’,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离骚》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叹其远而不得见之词也。”清人方玉润《诗经原始》解释道:“盖所挟者大,所见者远,故不禁有怀西京盛世,而慨然想慕文、武、成、康之至治不复得见于今日,因借美人以喻圣王,而独寄其遐思焉。”古今读者对此诗的理解差异很大。
本诗原为三章,朱熹改为四章。也有学者认为,本诗本为两首诗,末章单独为一首,后因错简被合为一首。本诗四章,韵脚如下:
第一章“舞”“处”属“鱼”部。第二章“俣”“舞”“虎”“组”属“鱼”部。第三章“籥”“翟”“爵”属“药”部。第四章“榛”“苓”“人”属“真”部。
【原诗】
北门
【注释】
[1]北门,城北门。
[2]殷殷,忧伤的样子。殷,又作“慇”(yīn)。《小雅·正月》有“念我独兮,忧心慇慇”。
[3]终,既。窭(jù),房屋简陋,无法行礼。贫,困于财。终……且……,相当于“既……又……”,如《邶风·燕燕》有“终温且惠”。
[4]已焉哉,算了吧。《卫风·氓》有“亦已焉哉”。
[5]谓之何哉,说它又有何用?无可奈何。
[6]王事,王室之事。后面“政事”指国家之事。适,本义是到,这里是归,意思是王事都归到我身上来。
[7]一,全。埤(pí)益,堆积。
[8]入自外,自外入,下班回家。
[9]室人,家里人。交,交替,轮番。徧,同“遍”,都。谪,责备,怪罪。
[10]敦(dūn),投掷,这里是扔给。一说逼迫。
[11]埤遗(wèi),意思同“埤益”。遗,加给。
[12]摧,排挤,打击。
【翻译】
我从都城北门出,内心忧伤无人诉。房舍简陋又穷困,无人体谅我心苦。算了吧!老天故意这样做,说它又有何用处!
王事已经归我扛,政事也都堆身上。下班离朝回家去,家人轮番将我谤。算了吧!老天故意这样做,说它又有何用场!
王事已经扔给我,政事也是我的活。下班离朝回家去,家人轮番排挤我。算了吧!老天故意这样做,说它也是无奈何!
【导读】
《毛诗序》说:“《北门》,刺仕不得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尔。”《郑笺》和朱熹《诗集传》也大体同此。
这就引起读者的疑问了:诗中的“我”挺受重用的,王事、政事都靠他来做,这不正是得志的证明吗?怎能说“不得志”呢?细看诗中“我”的忧怨,可能是“终窭且贫”。一个公务员整天忙得要死,俸禄却十分微薄,家里人难免会说些风凉话,严重的会指责“太傻”。干得多,得的少,这的确是一对矛盾。如果别人少干事,多拿钱,那就更让“我”的家人内心不平衡。看来,所谓“不得志”,大概是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吧。
再看“莫知我艰”四字,又觉得这个“我”一肚子委屈、忧伤,可是无人听他诉说,只能一个人憋在心中。这实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如果家里人不埋怨他,不指责他,而是鼓励他,安慰他,那会怎么样呢?“我”内心的痛苦一定会减轻。所以“不得志”的原因又不能完全归因于俸禄少。这个“我”思来想去,最后归结于天命。“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这几句写得真好!既然是命中注定,那就说了也白说,干脆不说。可是不说吧,心中实在憋得难受,于是写了出来。估计“我”就是这首诗的作者,这几句是描写他的心理。
今人评价《北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李山在《诗经析读》中写道:“《北门》,表现官场小人物牢骚满腹的诗篇……在一个小贵族自叹自怜的磨磨叨叨中,显示了社会生活的一副‘体段’,一股没出息的情绪。”兰波在《〈邶风·北门〉:小人长戚戚》[24]一文中说:“暴露了其“志”之褊狭与局促”。而刘毓庆在《诗经考评》中引用清代方宗诚《说诗章义》中的话:“极力述其苦,乃忽以‘已焉哉’三字撇开,笔意变幻。又归之‘天实为之’,将以上诸苦,一齐扫除。胸襟何等开阔!文境何等脱洒!”两种感受与评价有天壤之别。
笔者以为,此诗表达不被理解的痛苦。尽管“王事靡盬”会带来痛苦,但此诗中的“我”忙于公事,无论王事,还是政事,都是受信任、委重任的表现。由此可见“我”很能干,累一些,俸禄低一些,是正常的。古代如此,现在又何尝不是?家人的理解很重要。“我”累得要死,下班回家应该得到家人安慰才是,但是家人“谪我”“摧我”,喋喋不休,“我”有苦难言。不被理解,这才是痛苦的原因。此诗写得真实感人,体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诗风。
本诗共三章,韵脚如下:
第一章“门”“殷”“贫”“艰”属“文”部;“为”“何”属“歌”部。第二章“适”“益”“谪”属“锡”部;“为”“何”属“歌”部。第三章“敦”属“文”部,“遗”“摧”属“微”部,“微”“文”通韵;“为”“何”属“歌”部。
【原诗】
北风
【注释】
[1]其凉,即“凉凉”。这是起兴,用天气的寒冷引出生存环境的恶劣。
[2]雨(yù),动词,下(雪)。其雱(pāng),即“雱雱”,雪下得很大的样子。
[3]惠,爱,一说“顺”。而,相当于“然”。好我,喜欢我。
[4]行(háng),道。一说“去”。“同行”“同归”“同车”意思相同,都是一同离开。
[5]其,难道。虚,迟缓。邪(xú),通“徐”,缓慢。
[6]既,已经。亟(jí),紧急。只且(jū),语气词。
[7]其喈(jiē),即“喈喈”,风疾声大。一说同“湝”,寒冷。
[8]其霏,即“霏霏”,雪大的样子。
[9]莫赤匪狐,皮毛不红就不是狐狸。这是一个双重否定句,在于加强语气。莫,不。匪,非。
[10]莫黑匪乌,羽毛不黑就不是乌鸦。天下乌鸦一般黑。本句意思是,凡是暴政,一定危害百姓。乌,俗称乌鸦。
【翻译】
北风凄凉寒刺骨,大雪纷纷飘下土。如果爱我心相通,并肩携手去他处。难道还能慢慢走?情况紧急莫延误!
北风呼啸天气凉,大雪纷纷从天降。如果爱我心相通,并肩携手走他方。难道还能慢慢走?情况紧急莫彷徨!
皮毛不红非狐狸,天下乌鸦一般黑。如果爱我心相通,并肩携手出重围。难道还能慢慢走?情况紧急莫徘徊!
【导读】
同学们都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句俗语,若问其最早出处,应该出自《北风》。钱锺书在《管锥编》说:“按今谚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首诗是讽刺卫国统治者的。《毛诗序》曰:“《北风》,刺虐也。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焉。”《郑笺》曰:“寒凉之风,病害万物。兴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乱。”朱熹《诗集传》曰:“言北风雨雪,以比国家危乱将至,而气象愁惨也。故欲与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宽徐乎?彼其祸乱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至于“贤者避乱”之说,与百姓避乱之说本质相同,都在于说明政治环境的恶劣。
本诗运用了起兴的手法。“北风其凉,雨雪其雱”“北风其喈,雨雪其霏”,这四句写北风呼啸,大雪纷纷,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会遭受寒冷的侵袭。这是一般人的生活经验。所以,要想避寒,就需要到温暖的地方去。正是有了这样的“兴”,所以才有了下文“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携手同归”“携手同车”的呼朋引伴。你既然与我相好,咱们就共同逃离寒冷的天气,奔向温暖的地方。这些诗句在今天读来也觉得通俗易懂,但其含义深刻,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显然,天气不好,是隐喻,指政治环境恶劣。这从第三章可以看出。
第三章没有运用前两章以天气起兴的手法,而是换成了“莫赤匪狐,莫黑匪乌”,虽然也是起兴,但含义更加明显,由自然天气转向了动物。朱熹《诗集传》曰:“比也。狐,兽名,似犬,黄赤色。乌,鸦,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恶见者也。所见无非此物,则国将危乱可知。”为什么要这样变化呢?大概是作者担心读者误以为是躲避天气的寒冷吧?这样一换,诗的主题就彰显出来了。狐狸、乌鸦比喻统治者,他们对百姓残暴,就像冬天的寒风、大雪,会把人冻死。“其虚其邪?既亟只且!”这两句能引发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它似乎是说,朋友是犹豫的、彷徨的,甚至幻想等一等、看一看,统治者会变好的。而“我”是清醒的、理性的,呼吁朋友,认清形势,不要犹豫,不抱幻想,天下乌鸦一般黑。
对于“乌”意象的理解,有学者不这么认为,比如刘毓庆《诗经考评》认为:“感觉这更像一首有关婚恋的诗……推测当是女子出嫁后,忍受不了丈夫的虐待,此时有第三者介入,女子因此而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与之相约逃跑……”,李山《诗经析读》也持相近观点。但此说与古人观点相去甚远,且无本事可证,只能是“推测”而已。为了引发同学们的兴趣,笔者引用了李运富的另一种翻译,请同学们参考:
鹅毛大雪漫天翻,北风呼呼不觉寒。郎君真心喜欢我,驾车迎亲一起还。归心似箭嫌马慢,哪知四蹄已空悬!
北风呼呼声和悦,雪花悠悠舞随车。郎君真心来娶我,牵手坐车一起回。马儿为啥这样慢?全速飞奔不觉得!
不是赤红不算狐,没有黑色不是乌。郎君真心爱着我,驾车迎我同上途。莫怪马儿跑得慢?腿脚没有想象速!
笔者觉得还是应该尊重古人的观点。我们读《史记·卫康叔世家》得知,卫国虽然是小国,却内乱不断。国君荒淫,太子无德,臣子霸道,各种丑恶之事在历史上很出名,比如“杀兄继位”“州吁之乱”“宣公夺媳”“父子争位”“子路之死”,等等。可以说,卫国是春秋时期内乱持续时间最长的诸侯国。《诗经》中的《邶风》《卫风》《鄘风》所录作品其实都属于卫诗,《诗经》中那些揭露批判国君荒淫无耻的诗作,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写卫国国君的。还有故事说,子路要去卫国做大司马,孔子不赞成,就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个故事是否可靠且不说,但子路的确死于卫国内乱,被乱刀砍死,剁成肉酱。噩耗传到孔子那里,孔子家的厨师正在剁肉馅,孔子说:“倒掉吧。”孔子哪能吃得下呢!
《北风》这首小诗可以反映卫国政治,这从后代诗人的作品中也能看出。古乐府中有《北风行》,鲍照就写过《北风》,有“北风凉,雨雪雱……情易复,恨难追”之句,表达的是悲凉意境。李白有《北风行》一诗,末句写道:“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主题也是沉重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显然,范仲淹运用的手法与《邶风·北风》是一致的,这成为后世文人文学写作的常用手法。
柯小刚在《政教与自然:〈诗经·北风〉与变风的诗教意义》[25]一文中写道:“变风的意义不只是在控诉、怨刺、批判,而是也在提醒我们:正风的和美礼乐诚然是诗教追求的目标,可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诗人深知,家国礼乐、和美正风的存在前提却是有着巨大的、原始暴力的天地之大风。这或许是《北风》篇能给予政治哲学的永恒启发。”可以说,无论是诗歌的艺术形式,还是思想内容,《邶风·北风》都是一首现实主义的杰作。
本诗共三章,韵脚如下:
第一章“凉”“雱”“行”属“阳”部;“邪”“且”属“鱼”部。第二章“喈”属“脂”部,“霏”“归”属“微”部,“脂”“微”合韵;“邪”“且”属“鱼”部。第三章“狐”“乌”“车”“邪”“且”属“鱼”部。
【原诗】
静女
【注释】
[1]静,娴静。其,助词,放在单音节形容词前,属于衬音字。姝(shū),美丽。俟(sì),等待。于,在。城隅(yú),城角,或城的角楼。
[2]爱,同“薆”,隐蔽,隐藏。屈原《离骚》有“何琼佩之偃蹇兮,众然而蔽之”。见(xiàn),通“现”。袁行霈等《诗经国风新注》认为,若训“爱”为隐蔽之义,则主语当为女子,以“见”通“现”,于义为长。袁梅《诗经译注》(国风部分)也注通“现”。本书采用此说。搔首,用手指挠头。踟蹰(chí chú),徘徊。
[3]娈(luán),美好。贻(yí),赠。彤,红色。管,管状物。或说笔;或说乐器;或说草,即下文的“荑”。
[4]炜(wěi),红色而明亮。说怿(yuè yì),喜欢。说,同“悦”,喜爱。怿,欢喜。女(rǔ),同“汝”,指彤管。
[5]牧,郊外。归(kuì),同“馈”,赠。《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荑(tí),初生的茅。洵(xún),确实。异,出奇。
[6]匪,非。女(rǔ),指“荑”。美人,静女。
【翻译】
娴静女子好美丽,约我见面城角地。藏而不见在哪里?抓耳挠腮我心急!
娴静女子多美丽,送我彤管真情意。彤管红红晶透剔,握在手中心欢喜!
郊外采草赠我荑,荑草鲜嫩美无比。哪是荑草美无比,美人送我最甜蜜!
【导读】
《静女》入选高中语文课本,同学们一定很喜欢吧?是的,凡是读过这首诗的人大概没有不喜欢的。那么问一下,究竟喜欢它的什么呢?
诗中的静女太可爱了!尽管后人对“静”字有不同解说,但我还是觉得理解为“文静”为好。一般男子都喜欢文静的女孩,外表娴婉、柔美、庄重、高雅,令人想起那个“闲静时如姣花照水”的林妹妹,而配上一个“姝”字,就更加协调、舒适,这和老舍先生笔下的虎妞大异其趣。
不过,静也要分场合、看对象。热恋中的男女还是那样矜持、沉静,就不好了。俗话说“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看吧,“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静女提前来到约会地点,男友尚未到来,她灵机一动,故意隐藏起来。她想看一看男友找不到她会是什么样子。这是静女的可爱之处,调皮、灵动。
结果正如静女所料。男子来到约会地点后东张西望,南寻北觅,不见女友身影。他有点着急。喊吧?怕别人听到;找吧?又找不到。诗作者在此处用了四个绝妙的字:“搔首踟蹰”,于是一个憨态可掬的男子形象跃然纸上!读到这里,大概每一个读者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那个藏在隐蔽处的静女看着男友急得团团转、抓耳挠腮的样子一定乐不可支:你看他那傻乎乎的样儿!感谢诗作者天才地创造了一个词——“踟蹰”,从那时起,这个词便被后人频繁使用,直到今天。整首诗是以男子视角写的,“我”就是证据,但在此处,似乎换成了静女视角,好比镜头来回切换。笔者突然产生了一个感觉:作者自觉运用了风趣幽默的语言!两千年前的诗人呀,语言竟如此诙谐,这是怎样一个诗人呀?
也许静女笑出了声,男子听见后循声寻去,找到了心上人;也许静女突然跳出来大喊一声:“我在这儿!”这时的静女还文静吗?活脱脱就是一个顽皮活泼的女孩子,我似乎在蒲松龄《聊斋志异》中读到过这样的女子,却一时想不起是谁了。
这大概就是写人性吧?一个可爱女子的人性:文静与活泼的对立统一。这一情节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见面后,静女给男友亮出了爱情的信物:彤管。原来她是想给男友一个惊喜呀!彤管究竟是什么东西?有说赤笔的,有说乐器的,有说针管的,有说赤管草的,莫衷一是。欧阳修在《诗本义》中说“不知此彤管是何物”,朱熹在《诗集传》中也说“未详何物”。王力《古代汉语》认为,解释为红色管状的草即下文的“荑”较妥。同学们在语文课上不必去细究彤管为何物,只要懂得“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彤管代表我的心”即可。就是说,诗中男子表达感情的手法值得同学们学习。诗中写道:“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这里的“女”通“汝”。下同)这个男子很喜欢这个礼物,他拿在手中,看了又看,被彤管红亮的颜色吸引住,爱不释手。(“洵美”一词遂被后人所喜爱,有一个文人用这个词作为自己的名字,同学们在《拿来主义》中学过)男子打心眼里认为这个礼物不一般,它是二人爱情的象征!就在这时,末句“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结束了全诗。有人说这是爱屋及乌。我觉得更符合文艺理论中的“移情”。彤管也好,荑草也好,应该并不少见,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因为它是女友亲手送给的,那就非同寻常了。人的主观感情一旦投射到客观景物上,于是“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自古迄今,诗人常用这种手法。比如牛希济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再比如徐志摩“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这里的物与情不仅仅是联想使然,还因为诗人事先的经历赋予物特殊的情感。
我想到了孔子。这首《静女》孔子是读过的,尽管没有留下对此诗的评论,但是他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我对孔子这话颇有感慨。因为孔子之后有些人说《静女》之类的诗是“淫诗”,极尽贬低之能事。但是孔子肯定它们。我读《论语》读到“思无邪”,便遐想无限,于是一个场景出现在我的眼前:
一天,孔子正在翻阅刚刚整理完的《诗经》一书,他读到《》(jiōng)这首诗,反复吟诵着“思无邪”三个字,觉得很有意思。这时,子路和颜回两个人急急忙忙进来了,个个面红耳赤,看那样子,他们之间似乎刚刚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子路气鼓鼓地说:“先生,您来评评理,《诗经》中那些写男欢女爱的诗该不该删掉?您不是说过‘放郑声’吗?”颜回也很生气,这很少见,平时他总是文质彬彬的。颜回也气鼓鼓地说:“那些诗表达了男女真情实感,不能删掉!”孔子明白了,他和弟子整理的《诗经》一书中,有一部分是写男女爱情的诗,有的弟子建议删掉。孔子静了静,说:“我们整理《诗》三百,认真考察了每一首,并一一弦歌之,如果借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思无邪’。不删。”
今天,我们喜欢《诗经》,真得感谢孔子!由于他对《诗经》的悉心呵护,使得后世很多“陈最良们”无可奈何!即便刘向在《说苑·辨物》中引用此诗时也不得不承认它是表达男女情爱的诗作,写道:“乃陈情欲以歌。”
是不是说学术界都认为《静女》是爱情诗呢?不是。《毛诗序》认为“《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刺卫宣公纳伋妻也”。今人陈子展先生在《诗经直解》中说:“彤管为女史载事记过之笔”。最早引用《静女》诗句的古代文献大概是《左传》一书。《左传·定公九年》:“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由此可见,“彤管”在《左传》那里属于正义形象加以肯定。所以,对上述种种非爱情说不能轻易否定,或许有本事可据。特别是在《诗经·邶风》中将《静女》与《新台》《二子乘舟》排在一起,前后形成一个批判组诗也未可知。
全诗共三章,韵脚如下:
第一章“姝”“隅”“蹰”属“侯”部。第二章“娈”“管”属“元”部;“炜”属“微”部,“美”属“脂”部,“微”“脂”合韵。第三章“荑”“美”属“脂”部;“异”属“职”部,“贻”属“之”部,“职”“之”通韵。
【原诗】
新台
【注释】
[1]新台,卫宣公在黄河岸边修建的高大建筑。靠水的建筑为台。泚(cǐ),鲜明。一作“玼”。
[2]河,黄河。㳽㳽(mí),河水盛大的样子。
[3]燕婉,美好漂亮的人。之,句中助词。求,求配偶。
[4]籧篨(qú chú),身体残疾,驼背鸡胸。一说癞蛤蟆。鲜,好。
[5]洒(cuǐ),高峻。
[6]浼浼(měi měi),河水盛大。
[7]殄(tiǎn),美善。
[8]设,设置。
[9]鸿,蛤蟆。一说大雁。离(lì),附着。
[10]戚施(yì),驼背的残疾人。闻一多认为“戚施”“籧篨”“鸿”当为一物,即癞蛤蟆。
【翻译】
新台新台鲜又亮,河水河水大又涨。本想嫁个帅小伙,哪知遇上蛤蟆郎。
新台新台高又高,河水河水大又涨。本想嫁个帅小伙,倒霉遇上蛤蟆郎。
张网本想得大鱼,不想来了蛤蟆郎。打算嫁个帅小伙,嫁给驼背我心伤。
【导读】
《新台》是讽刺卫宣公夺媳丑行的一首诗。据《左传·桓公十六年》记载:“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卫宣公是个荒淫无耻之君。他先与其父之妾夷姜通奸,生儿子急子(也叫伋子)。后来,宣公为伋子娶了一位齐国女子,发现太美了,于是占为己有,并安置在新台这个豪华的建筑中,金屋藏娇,就是后来的宣姜。上烝庶母,下夺子妻,成语“上烝下报”由此而来。卫宣公真是荒淫到了极点,百姓看不下去,于是写了《新台》,讽刺卫宣公,说他是个癞蛤蟆。《毛诗序》说得更明白:“《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司马迁《史记·卫康叔世家》以及《郑笺》《诗集传》都持此说。也就是说,在肯定此诗讽刺卫宣公这一点上,以上诸家没有异议。
敢于讽刺统治者的荒淫无道,这既是《新台》一诗作者的胆量,也是后世《诗经》研究者的求实态度,丝毫没有为尊者讳。《诗经》之所以伟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现实主义诗风,向上揭露批判统治者的丑恶行为,向下反映民生疾苦,为后世诗人树立了诗歌创作的典范,使得中国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了高尚的灵魂。唐代诗人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就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新台》的作者是谁?是不是宣姜本人呢?不会的,因为那样会危及她的生命安全。笔者推测,应当是民间有文才的人。卫宣公身边的人大概不敢写。百姓看不下去,便口耳相传,然后文人记录下来,于是形成此诗。那为何能入选《诗经》呢?这就说到“变风”了。《诗大序》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从“正风”到“变风”直接反映了周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变化。中国文学,向来记录历史,《诗经》的内容经历了“礼教”“乐教”“政教”“德教”“诗教”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是复杂交错的,但总体发展趋势是清晰的。
本诗共三章,韵脚如下:
第一章“泚”“㳽”属“脂”部,“鲜”属“元”部,“脂”“元”合韵。第二章“洒”“浼”“殄”属“文”部。第三章“离”“施”属“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