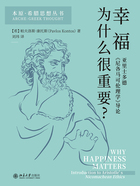
1.5 幸福的标准(I.7)
我们的目标是定义幸福,在I.5里面我们已经达到了某种结论,把不同的人生当作我们的经验基础。然而,这种进路也只能把我们带到这里了。我们还需要一些标准帮助我们用更精确的方式去回答幸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让我们称之为形式化的标准,因为在第一卷里它们并不能告诉我们幸福是什么,而只能告诉我们要如何构造它。这些标准就像语法或者句法规则一样,规定着我们对幸福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这些规则尊重或者再现了幸福本身的结构。
在考察这些标准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已经获得了什么。我们知道了幸福与人的实现活动或行动联系在一起,而这些行动是由它们的目的(telos)定义的。因此,要评价人的行动,我们需要比较性地评价它们的目的。这样,我们就要对这些目的进行分类,一个基于完满性的以最高目的为归宿的等级序列,这个最高的目的是完满的目的或者完满的完满(perfect perfection, teleion telos)。我们肯定会问,有什么形式化的标准可以帮助我们比较目的吗,人类行动的目的真的可以比较吗?亚里士多德在下面的文本中给出了三个形式化的标准:
I.7.1097a30-1097b20:【1】我们说,内在地值得追求的东西比因为其他东西而值得追求的更完满,从不因为其他东西而值得选择的东西比既因为自身又因为它而值得选择的东西更完满,因此,最无条件地完满的东西就总是内在地值得选择,而绝不会因为其他东西而值得选择。幸福看起来最像这样……【2】从自足性(self-sufficiency)上显然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因为完满的好看起来是自足的。【2a】然而,我们说的“自足”并不是对于某个独自生活的人的自足,而是普遍而言对于父母、孩子、妻子、朋友、同胞公民的自足,因为人依据自然是政治性的……【2b】我们认为,自足本身让人生值得过并且无所缺失,幸福就是这样的。【3】此外,我们认为,当幸福不是被当作诸多事物中的一个,它就是最值得选择的。但是如果它被放在它们当中计算,那么很显然,哪怕加上最小的好也会更值得选择;或者增加的东西会带来更多的好,对于好而言,更大的总是更值得选择的。
【1】里面的提到的标准看起来让人困惑,亚里士多德在区分三种不同的好。我们可以称第一种为工具性的好,我们选择它们是为了其他的东西。比如,工匠制作马嚼子,马嚼子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对骑手而言有用,如果这种有用性不再存在,那么马嚼子也就不再有用。这是最低等级的好。另一些好可以说是复合型的好,它们既因为本身又因为对某些其他东西有用而有价值。比如,公共的承认本身是有价值或者美的,但同时它也在工具的意义上有用,因为它让我们更容易从事有价值的政治活动。这意味着虽然它很重要,但是它不如作为目的的那个好有价值。因此,问题就在于,是否存在一些好,它们本身有价值,但是完全不服务于进一步的目的。这个完全不服务于更好目的的好就是完满的好。我们不知道这些完满的好是什么,有很多还是只有一个,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否存在。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在探索这个问题,既然存在好的等级,必然存在一个或多个最高的好作为顶点。
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好的唯一例子就是幸福,因为我们认为问幸福服务于什么目的是不合理的,因为它解释了所有其他的好而没有被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解释。“你为什么想要幸福?”或者“幸福的目的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完全无需回答。然而正是这一点让幸福如此难以把握:一个在任何时间都更值得选择,而且仅仅因为它自身而值得选择的好,是很难理解的。不管怎样,这第一个标准并没有给我们任何关于幸福内容和可能性的观点。
【2】讨论的标准来自我们共有的经验,它把完满性与自足性联系在一起,如果某物需要其他东西,那么它就有所缺失,因此不是完满的。自足可以用两种方式理解。一种是【2a】里面描绘的情况 1,即一个自足的人脱离政治社会独自生活。但这个理解是错误的,这种自足对于人来讲是不可能的,既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不可能,因为没有人是自己长大的,我们需要父母;也在社会的意义上不可能,因为没有人可以由于自然的因素在脱离政治共同体的情况下完全成熟。因此【2b】给出了另一种理解,把自足理解为,有了它人生就值得选择,不需要任何额外的东西。然而,这又引向了一个死胡同,不管一个行动多么自足,人至少都需要健康和营养,从而可以实现自己的行动(X.8.1178b33-35)。因此,将完满和自足等同,必然要用一种更加具有灵活性的方式重新表达,对人类而言,一个行动越是自足,它就越完满,即便最完满的行动对我们来讲也不是绝对自足的。绝对的自足是神的特权。
要用最精确的方式理解人类行动的自足,我们必须要引入“外在的好”(external good)这个概念。它们是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它们的价值外在于与之对应的行动。亚里士多德说的财富就是一种外在的好,因为如果我们负担不起生活所需,就需要花全部时间去追求物质性的好,而无暇从事其他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财富影响着全部人生,并且保证了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闲暇(scholê):不必被迫为了生计奔忙,而是可以致力于我们认为重要的或者有意义的行动。财富还在另一个意义上是外在的好:只有当一个人拥有一定的物质财富可以给予他人时,他才是慷慨的。当然,慷慨的价值并不来自物质财富,然而物质财富也是“给予”这个行动的组成部分。慷慨的行动依赖财富,如果没有财富,他们的自足性就会受到减损。因此,第二个标准让我们去寻找最不依赖外在好的行动。
在【3】里面讲到的第三个标准不太容易理解:在所有的行动中,最值得选择的行动不是和与它比较的其他的好放在一起计算的。否则,假如可以在幸福(H)之上加上某个好(G),那么就会得到G+H>H,因为两个好的和总是大于其中任何一个,而不管G的初始价值多么小。这样一来,每个人就都会想要得到幸福加上某个其他东西,而这与幸福是最高的好相矛盾。2
因此,亚里士多德就要说明,我们不能把幸福和某个其他的好想像成G+H的样子。可以用两种方式理解这一点。一种是主张幸福与其他的好种类完全不同,这样一来,幸福就不能因为加上了其他好而变得更好,所以G+H就是毫无意义的,就像我们说“猫+2”没有意义一样。第二个策略是认为,幸福说的不是某一个行动,而是全部有价值的行动的总和,也就是所有好的总和,因此没有任何好在这个总和之外,也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加在幸福之上。第一个阐释经常被称为“排他论”(exclusivism),第二个被称为“包容论”(inclusivism)。在I.7里面,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明确支持任何一种阐释,虽然坚持自足的概念,以及提到最好的和最完全的德性,可能会被认为是暗暗支持第一种阐释。重要的是,我们有一条形式化的规则反对G+H是比H更大的好。
不管怎样,我们考察的这三条规则并没有把我们限制在对幸福内容的任何具体理解上,它们只是给出了幸福的语法和句法规则。
1 【2a】这句话的句法有些出人意料。我们期望中的与独自生活相反的是和朋友、孩子等在一起的生活。然而亚里士多德并不是这么说的,而是把自足归给了孩子、父母等。这么说很奇怪,特别是因为包含了孩子。但是不管怎样,他的意思是我们意料中的。或许我们应该把自足理解成必然包括了某人的孩子和父母,或者是我们孩子或者朋友的遭遇不可能让我们无动于衷。现在最古老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注疏者阿斯帕西乌斯(Aspasius)就是这样理解的(CAG XIX: 16.11-22)。
2 也有学者认为,【3】给出的不是一个独立的标准,而是对“自足性”的进一步说明,即这里说到的“自足”不是简单的量上的毫无缺失。如果这样理解,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就是给出了两个(而非三个)界定幸福的“形式化标准”。——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