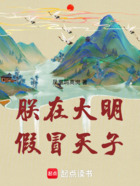
第68章 不以旧恶掩新罪
张祁轻抿嘴角,“然则,廖永忠虽在开国后获封德庆侯,却在洪武八年被太祖皇帝赐死,成了太祖皇帝诛杀的第一个开国功臣,这般结局,又怎能佐证太祖的用人之智呢?”
于谦从容应道,“廖永忠之死,实因其僭越礼制,擅用龙凤等违禁之物,触犯国法,故而伏诛,与小明王案并无干系,正因如此,方显太祖皇帝处事分明,赏罚有度,不以旧恶掩新罪。”
张祁听罢,心中却愈发觉得朱元璋此举实有过河拆桥之嫌。
不管廖永忠当初是出于何种考量,在诛杀韩林儿一事上,绝对算是向朱元璋表了忠心。
朱元璋非但不念其功,反而以“僭用龙凤”这等莫须有的罪名将其赐死,实在令人心寒。
倘或当年廖永安兄弟并未投奔朱元璋,而是效仿陈友谅、张士诚割据一方,以其巢湖水师之强,未必不能成就一番霸业。
难怪明末流寇四起之时,再无元末那般天下豪杰率众投效农民军的景象。
朱元璋这般对待功臣,早就把农民军的信誉都给透支殆尽了,致使后来者对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望而却步,最终反倒让满清坐收渔利。
然而这番心思,张祁终究不便明言。
其一,于谦等人尚不知李自成为何许人,更无从理解朱元璋屠杀功臣之举,为汉人埋下了怎样的祸根。
其二,他心知肚明,于谦此言不仅是在宽慰他,更是在暗中为王竑转圜。
毕竟若他当真介怀,大可以效法朱元璋,日后随便寻个由头处置了王竑。
须知以张祁如今之权柄,此事不过在他一念之间。
但从理智上来讲,张祁不该处置王竑,王竑虽只在郕王府“观政”数载,却是少数能与潜邸旧臣攀上关系的朝臣。
若因一时意气将其贬黜,他那本就单薄的亲信圈子,只怕更要捉襟见肘了。
而且张祁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挥之不去的疑虑,陈镒当廷弹劾王振,王竑怒殴马顺,这两桩轰动朝野的大事,背后是否都有于谦的影子?
虽然弹劾王振一事,确实是在他提议立储时,由于谦顺势提出,且得到了孙太后的首肯。
但具体如何发难、何时发难,这些关键细节,此次朝会前他却全然不知情。
后世史书只将此事归因为王振平日作恶多端,众臣激于义愤而群起攻之。
然而张祁总觉得,这看似偶然的爆发,实则是于谦在幕后精心排布的一个局。
倘或此局确系于谦所设,倒也无可厚非。
真正令张祁坐立难安的是,这明明是为自己立威铺路的谋划,于谦却始终讳莫如深。
此中深意,显然不止助他蜕变为真正的郕王朱祁钰这般简单,分明是在试探他的为人。
回想前事,该杀马顺时他犹豫不决,借南迁之议裹挟于谦支持立储,又欲借王振一案株连王骥……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让于谦不得不设局试探,他张祁究竟是心怀城府的伪君子,还是真具仁德的明主?
当然这只是张祁个人的猜测,于谦断然不会承认“午门血案”乃是为试探他而设的局。
可正因这份难以言说的猜疑,让张祁心头总存着几分郁结。
更令他踌躇的是,于谦已将姿态放得极低,甚至以“不以旧恶掩新罪”为朱元璋诛杀廖永忠开脱。
其言下之意即是,太祖皇帝可以不念廖永忠诛杀小明王的忠心,殿下自然也可以不记我于谦诛除王振、马顺为您立威的功劳。
他日若我于谦行事有违殿下心意,殿下大可效法太祖皇帝故事处置于我,我绝无怨言。
张祁扪心自问,若易地而处,自己决计做不到于谦这个地步。
如此情形下,自己若还要追根究底,岂非显得不识好歹?
张祁终究没有再出言反驳。
此刻他心底竟隐隐生出几分对于谦的惧意,穿越之前,他总以为是孙太后构陷忠良,如今再看,孙太后斥责于谦为“奸臣擅谋”之语,也未必全是污蔑。
他不敢,也不能冒险触怒这位深不可测的能臣。
于谦又关切地询问了几句张祁的身体状况,见他确实已无大碍,这才稍显安心。
恰逢服药时辰,朱祁钰的旧日心腹宦官王诚捧着药碗入得房中,
于谦竟亲自接过药碗,欲要侍奉汤药。
张祁顿觉浑身不自在,这与史书中那个刚正不阿、不事谄媚的于谦形象大相径庭,他心中警铃大作,连忙推辞道,“本王已痊愈,这药就不必再用了。”
“况且侍疾这等琐事,自有王妃或内侍代劳,岂敢劳动大司马亲自动手?”
张輗正色劝道,“殿下此言差矣,此乃太医院精心配制的汤药,须得服完整个疗程方见成效。”
张䡇亦附和道,“正是,先前殿下昏沉不醒时,皆是我兄弟二人亲侍汤药,连王妃与内侍都不曾假手,今日大司马亲临,殿下何不成全大司马的这番心意?”
张祁一听是太医院开的药,更加不敢吃了。
明朝太医中,除李时珍等凤毛麟角的名医外,其余大多医术堪忧。
这其中的症结,正在于明朝太医院荒谬的选才之道,其医官来源不外乎医户世袭、地方保举与捐纳买官,每一个途径都弊端丛生。
所谓“医户”,乃承袭自大明的户籍制度。
天下户籍分为军户、民户、匠户三大类,其中民户又细分为儒户、医户、阴阳户三种。
医户子弟须世代行医,不得改业,朝廷每三年对医户子弟进行考核,十五岁以上者先考为“医丁”,再经太医院复试合格方可为“医士”,三次落第者,则永革考试资格,遣返原籍。
李时珍便是出身这般医户世家,其父曾任太医院吏目。
然这般世袭制度,至明中后期已形同虚设。
于是又开“外访保举”一途,由州县官员举荐当地良医,经礼部与太医院考核便可入太医院任职,然因举荐者需负连带之责,致使地方官畏葸不前,故而应者寥寥。
最不堪者当属“捐纳”,朝廷财政吃紧时,公然卖官鬻爵,医士一职亦可花钱捐得,致使太医院良莠不齐,庸医充斥。
即便是在正统年间,太医院中保举与捐纳的医官尚属少数,但张祁对所谓“医户世家”出身的太医同样心存戒备。
细数明朝前中期的几位皇帝,除了景泰帝死因成谜之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乃至后来的明宪宗、明孝宗,皆是壮年病亡。
后世人推测,明仁宗与明宣宗或罹患消渴症,这个病即使放在现代医学条件下亦属顽疾,需要精心调治。
然明英宗、明宪宗、明孝宗所患不过寻常病症,若在现代,几剂抗生素便可痊愈,却生生被太医治成了不治之症。
这让张祁如何还敢轻信这明朝太医的医术呢?
何况作为一个现代人,他对这些熬煮草药的汤剂本就心存疑虑,将一堆植物根茎丢进砂锅煎煮,滤去残渣后的浑浊汤水,既说不清具体成分,又道不明药理机制,真的能通过现代医学的双盲对照试验吗?
而且不少中药药材长期服用会导致肝肾损伤,那些看似温和的植物碱在体内日积月累,其毒性未必比道士炼丹的汞铅之毒轻多少。
太医院这些所谓的“良方”,在他眼中不过是文火慢煎的慢性毒药罢了。
自己这三日病愈,全赖这副身躯原本的抵抗力,与那太医院的苦汤药实在没多大干系。
可这般道理,要如何与眼前这三位明朝土著解释?
若要细说分明,非得从现代医学的解剖学说起,再论及细菌病毒和人体免疫系统,这样一扯,又不得不牵扯到自己穿越的离奇经历。
这一环扣一环,只怕是越解释越让人糊涂。
张祁眸光微动,心念电转间已有了计较。
他既不愿解释病愈原委,又觉于谦今日殷勤太过反常,索性开门见山道,“如今王振伏诛,马顺已死,本王亦赦免了群臣当庭殴杀之罪,大司马如此殷勤侍药,莫非又有所求?”
果然,于谦搁下药碗,神色凝重道,“下官先前进来时未敢直言,唯恐再惊扰殿下,王振之侄,锦衣卫指挥使王山业已伏诛,身受凌迟之刑。”
“马顺、毛贵、王长随三人尸首现已悬于东安门示众,往来军民无不切齿痛恨,争相击打以泄愤恨,现下朝臣联名上奏,奏请籍没毛贵、王长随家产,正待殿下朱批,早降令旨。”
张祁听罢,午门前那血肉横飞的血腥场景又浮现在眼前,马顺三人尸身早已不成人形,如今竟又被悬于东安门示众,那又该是何模样?
他忽想起石亨先前的奏报,京师官民匠作不下百万之众。
即便京城中仅有百分之一的人仇视王振党羽,那也是上万之数。
每人一记扁担、一棍铁锹,最不济也有一根擀面杖,那一人一棍下去,莫说是血肉之躯,就是铜浇铁铸的罗汉也经不住这般捶打。
打不到一半人就得把这三具尸体夯个稀巴烂。
张祁强忍眩晕,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三具尸骸眼下的惨状。
头颅如破碎的瓜果般凹陷变形,歪斜地耷拉着,乌黑的血浆凝结在七窍之间。
原本狰狞的面容如今只剩一团模糊血肉,数不清的棍棒痕迹深深嵌入皮肉,将整张脸砸得稀烂。
脖颈被绳索勒得乌紫肿胀,舌头吐出寸余,双目圆睁,却早已被乱石砸得眼珠爆裂。
双臂自肩胛处断裂,仅余几缕筋肉牵连,随着秋风无力摆动。
胸腹处完全塌陷,肋骨根根外露,犹如被猛兽啃噬过的残骸。
……
再一想,不对不对!
吊在东安门上,那不应该是头更高吗?
擀面杖够不着,先从脚踝骨打起,一点点打到膝盖。
那最先遭殃的便是那悬垂的双足,趾骨最先碎裂,接着是脚掌,最后整只脚就像被捣烂的柿子。
接下来膝盖成了新的目标,坚硬的膝盖骨在雨点般的敲击下渐渐龟裂,继而“咔嚓”一声彻底粉碎。
失去支撑的小腿顿时软塌塌地垂下来。
像条装满骨渣的破麻袋,随着每次击打诡异地晃动着。
待双腿尽毁,便转向了手肘关节,这里的皮肉较薄,没几下就被打得皮开肉绽。
白森森的尺骨桡骨从糜烂的肌肉中支棱出来,很快也被砸成碎渣。
暗红的内脏碎末混着骨髓,像黏稠的糖浆般顺着残肢缓缓滴落,在青石板路上积成三滩散发着腥臭的血泊。
……
张祁要吐似的一弓身子,一阵剧烈的干呕让他眼前发黑。
胃里早已空空如也,却仍止不住地痉挛,只能吐出几口酸苦的胆汁。
他分不清自己这是同情心过剩,还是想象力过于丰富,那血腥的画面如同附骨之疽,即便时隔三日粒米未进,只要稍一回想,五脏六腑便又翻江倒海般绞痛起来。
张輗与张䡇见张祁又欲作呕,慌忙四下寻摸痰盂,一时间手忙脚乱。
于谦见状,不由轻叹一声,道,“此事本是顺应民心之举,未料殿下如此不忍闻听,故而下官原想着先侍奉殿下用药,待殿下身体稍安,再行禀报。”
张祁伏在痰盂边干呕数声,只吐出些许酸水,他虚弱地抬起手,朝于谦无力地摆了摆,“罢了,人既已死,何必再行抄没?毛贵、王长随落得如此下场,警示之效已然足够,他们二人本不在陈镒弹劾之列,实属无妄之灾。”
“况且皇太后殿下有言在先,不当株连过甚,若定要抄家,只按陈镒奏疏所列,查抄宦官郭敬、陈璵、唐童,钦天监正彭德清等人家产便是。”
于谦目光深沉地看着张祁,他沉吟片刻,又拱手道,“下官还有一事要禀奏殿下,陈镒奉殿下令旨查抄王振家产,所得之数,实在骇人听闻。”
“王振宅邸数处,其富丽堂皇竟可比拟宫阙内苑,所用器皿服饰、珍玩古物,连尚方监都相形见绌。”
“单是径尺玉盘就有十面之多,还有七八尺高的珊瑚树数株,更查得金银库房十余座,骏马良驹万匹有余,如此巨资,不知殿下欲作何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