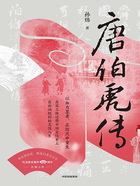
第二节 少年时代的挚友
虽然有关唐伯虎早年的史料很少,但我们依旧能从蛛丝马迹中了解到他青少年时期的一些情况。比如他学习成绩十分优异,但性格孤傲,不喜与外人交往。唐伯虎少年时代最要好的朋友有三位——刘嘉䋭、张灵和文徵明。他们性格迥异,在当时都很有名。
◇发小刘嘉䋭◇
刘嘉䋭出生于成化四年(1468年),比唐伯虎大两岁,是官宦子弟,也住在吴趋里的皋桥,是唐伯虎的发小和邻居。少年时代的刘嘉䋭长得白白净净,眉清目秀,举止稳重,而且读书用功,在大人们眼里是个伶俐乖巧的孩子。人们夸赞他“年数岁,据小几习书,俨然成文。又选古诗,模其格律,皆有妙悟”[1],有点少年老成的模样。
刘嘉䋭的父亲刘昌,字钦谟,“为世大儒,著书甚富”[2],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刘昌官广东左参政,任上因病去职,回乡后便去世。刘昌之墓挨着一座古墓——南宋副宰相范成大的墓。刘嘉䋭每年清明为父亲扫墓,总能看见范成大的那座墓被盗。盗墓贼跟钟摆似的,去年刚走了一拨,今年又来另一拨。刘嘉䋭感慨不已,于是摇笔一挥写成《吊范墓文》,此文受到众人一致赞扬。唐伯虎说他“作文吊之,摇笔立成,词不加窜,虽老成宿德,莫不推其博雅”[3]。可见刘嘉䋭年纪虽小,文笔不俗,深孚众望。
十六岁以前的唐伯虎,身边除了刘嘉䋭之外,好像再也看不到其他形影相随的好伙伴了。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唐伯虎整天跟刘嘉䋭这样的好学生在一起,也应该是个中规中矩的读书好儿郎。尽管刘嘉䋭比唐伯虎年长,读书也更刻苦,但他的学习成绩却不如后者。这虽然还不足以证明少年唐伯虎是天才,但至少说明唐伯虎更擅长科举考试。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唐伯虎时年十六岁,他与十八岁的好友刘嘉䋭一起参加了至关重要的考试,即童生试。童生试分为三个阶段,最终唐伯虎通过考试,补为府学附生。
明朝的童生试分为县试、府试和院试,是科举道路上最低的三道门槛,只有通过以上考试的学子,才能以秀才(生员)的身份参加下一轮的岁试、科试,争取参加乡试的机会。在乡试中考中举人,才有可能被朝廷选派去当官。
由吴县知县主持的县试,算是童生试的第一道门槛,其难度还是蛮高的,许多读书人从青丝考到白发,甚至带着孙子一起赴考,都未必能通过。而一旦通过童生试的全部考试成为秀才,就能享受免除差徭、见官不跪、被告入狱时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
唐伯虎自此在苏州学界有了声名。当然,这主要是指在读书人的科举圈子里,此时的他还未走入社会。
数年后,徐祯卿也成为刘嘉䋭的好朋友。因为家穷买不起书,他经常来找刘嘉䋭借书。正是在刘嘉䋭家里,他认识了一生的第一知己唐伯虎。
◇酒友张灵◇
唐伯虎的第二位腻友,是“家与唐寅为邻,两人志气雅合,茂才相敌”[4]的张灵。张灵,字梦晋,是个内心寂寞而又性格叛逆的少年。
张灵与唐伯虎年龄相仿,他俩开始交往的时间是成化二十一年。这时两人同时考进了府学,成为同学。这个时候的张灵,虽然也是个出色的秀才,可他身边却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张灵的身世与刘嘉䋭、唐伯虎完全不同。刘嘉䋭是个官宦子弟,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处处受人礼遇;唐伯虎家境小康,学业优秀,万事不求人,也有点儿自视清高,不愿意与别人交往;而张灵是个苦出身,家境贫寒,这使得世俗之人本来就从心底里怠慢他,不爱与他来往,可张灵偏偏又是个倔强之人,别人不把他放眼里,他更看不起别人,还动辄语出伤人,这使得乡党都很鄙视他,将其斥为轻薄放荡之徒。[5]整个苏州城里只有宽厚的祝允明礼待他。他觉得张灵有才气,尤其善于绘画,于是在成化二十年(1484年)将张灵招为门生。[6]拜师那一年,张灵还未考入府学,所以唐伯虎并不知道张灵是何方神圣。
张灵与唐伯虎本是邻居,以前怎么会不相识呢?住过弄堂的人都知道,邻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至少应该是面熟的。这只能说明,这哥俩都很高傲,目中无人,彼此视而不见。

◆明 张灵 《织女图轴》,现藏上海博物馆
家庭背景迥异的二人,又同处青春期,其实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比如,他俩都是具有才华的少年,自视清高,不愿受繁文缛节束缚,又都对绘画和饮酒有着强烈的热爱。王穉登在《吴郡丹青志》里说得客气了一点,“张灵性放诞……两人(张灵与唐寅)志气雅合”。其实,二人一相识,就像已经憋了许久,终于找到了可以撒尿的夜壶,额手相庆,感觉十分投缘,转眼之间就成了挚友。
唐伯虎和张灵一起做出了种种令读书人不可思议的事,不仅犯忌讳,还遭人鄙视,我们不妨来见识一下他俩离经叛道的种种表现。
苏州府学内有个泮池,也称“泮宫之池”,是府学的“配套建筑”,一般以石为岸,池水不深,就是一个大池塘,池边还长了些野芹,中间建有一座桥梁,通向正殿,类似官学的地理标志。某日,唐伯虎和张灵两人一时兴起,竟然当众脱掉衣服,赤条条跳入水里,“赤立泮池中,以手激水相斗,谓之水战”[7],玩得忘乎所以,十分尽兴。
府学本是读书人心中的圣地,孔子的塑像还立在大成殿内,以督促后学者克己复礼。师生们进入学府,理应个个整衣修面,笑不露齿,温文尔雅地说话,以保持谦谦学子的模样。泮池在读书人眼里,也具有神圣的意义。《诗经·鲁颂·泮水》写道:“思乐泮水,薄采其芹。”读书人考中秀才之后,均要来孔庙举行拜祭仪式:从泮池中采撷水芹,插在帽子上,庆贺自己成为真正的生员。在同样庄严的地方,且在孔子的眼皮子底下,唐伯虎和张灵竟然做出如此荒唐不雅的事,师生纷纷投以鄙夷的目光。府学里的长辈劝告道,尔等“不可以苏狂赵邪比也!”[8],大意是:你们这俩小畜生,胡子尚未硬朗,岂敢跟历史上的大名士比狂傲!
他俩还有个酗酒的嗜好,每饮必醉。张灵酩酊大醉之后,还要跟晚唐才子皮日休较劲,狂呼乱吼道:皮日休,你个老小儿,妄称醉士!你可以醉,难道我不能吗!一副颟顸不堪的模样。
因为是邻居,唐伯虎经常去找张灵玩。据说,每次唐伯虎推开门,都会见到张灵赖在被窝里,龟缩一团。唐伯虎就大声笑道:“太阳已经照到你屁股上喽,怎么还不起床?”张灵无精打采,嘟囔道:“今日无酒,雅怀不启。不如躺着,可以进入醉乡。”唐伯虎赶紧说:“我来找你,正是为了邀请你喝酒去。”张灵这才露出笑脸,一骨碌披衣起床,趿拉着鞋就去痛饮。[9]饮至方酣,也不管刮风下雪,两人总要扮作乞丐,再来一段“莲花落”说唱小曲,得意忘形时还说:“吾等不可以让李白看见啊,否则他会嫉妒的!”路人见此,恍如看戏,于是给了他俩一些赏钱。拿了赏钱,两人一扭头再去酒馆继续喝酒。
十七八岁的年纪如此放诞,二人自然成了人们调笑的对象。有些商人恶作剧,常常邀请他俩去喝酒,实际上是想看他俩出洋相。有一次,一些读过诗书的商人,在苏州著名景点虎丘的可中亭内摆下宴席,吟诗饮酒,故意将一些生僻的典故藏在诗里,比如“苍官”“青士”“扑握”“伊尼”等,然后考问张灵。张灵一扬脖子喝干了酒,随口答道:“苍官,松也;青士,竹也;扑握,兔也;伊尼,鹿也。”然后取笔挥毫,一口气写下很多诗篇,令商人们大为惊叹。张灵和唐伯虎趁机起身,悄悄上船,叫童子把船摇到隐蔽处。商人们寻找不见,便说他俩是神仙下凡,悻悻而去。[10]

◆明 张灵 《霜林行旅》扇面,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张灵家穷却又馋酒,遇到没人请酒时,就径直去别人家里讨酒。然而他傲物,又不讲礼貌,闹出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有一次他造访一户人家,坐到豆棚下举杯就饮,根本不看主人的脸色。主人自然很生气,遇到唐伯虎,知道他俩关系友善,就说起此事。岂料唐伯虎竟然翻起了白眼,对那人说:“你这算什么意思?难道是在嘲笑我吗!”弄得那人哭笑不得,拂袖而去。[11]可见他俩真是臭味相投的一对活宝。
虽然在后世文人笔下,生活中的唐伯虎与张灵让人啼笑皆非,但在真实历史中,他俩的绘画水平在年轻人中确实出类拔萃。张灵擅长画人物,亦间作山水。据《吴郡丹青志》载:“张灵………两人志气雅合,茂才相敌,又俱善画,以故契深椒兰。灵画人物,冠服玄古,形色清真,无卑庸之气。山水间作,虽不由闲习,而笔生墨劲,斩然绝尘,多可尚者。”年轻时,张灵的画作就可以在市场上出售,本可以此改善生活,然而他却整天泡在酒缸中,不能自拔。旁人不无遗憾地感叹,张灵“性落魄,简绝礼文。得钱沽酒,不问生业,嘐嘐然有古狂士之风。为郡诸生,竟以狂废”[12]。
唐伯虎家境优渥,而且父亲也给予了他坚定又慷慨的支持,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没有感到生活的压力,不必为生计卖画。当然,唐伯虎的才学和绘画水平,也要优于张灵。明代王世贞说:“张(灵)才大不及唐(寅),而放诞过之。”[13]
◇一生知己文徵明◇
唐伯虎的第三位知己,就是后来名贯古今的文徵明。在历史上,文徵明与唐伯虎齐名,而他的名气能远远大于刘嘉䋭、张灵之辈,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显然是他长寿。长寿是艺术家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旦同辈艺术家纷纷下世,长寿的艺术家必然被晚辈尊崇为泰斗。文徵明就是这样一位典型。
文徵明的身世比较复杂,须细细道来。

◆明 佚名 《文待诏小像》现藏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
文徵明生于成化六年,依公历算,具体日期是1470年11月28日,只比同庚的唐伯虎小8个多月。他出生在苏州城德庆桥西北曹家巷的一户官宦人家。家有薄产,也属小康。
文家颇有来头。远的不说,文徵明的六世祖文俊卿有六个儿子,其中次子文定聪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亲兵,被朱元璋的重要将领蔡本招赘为婿。蔡本是武官,洪武七年(1374年)担任正三品的苏州卫指挥;到了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升为正二品的浙江卫指挥,卒于任上。这个人凶险狡诈,在担任苏州卫指挥时,曾构陷苏州知府魏观和长洲著名文人高启图谋不轨,导致魏观和高启被冤杀,因此蔡本为后人所不齿。
文定聪就是文徵明的五世祖。他跟随岳父蔡本去了杭州。文定聪所生的四个儿子中只有老二文惠继承了文定聪的“传统”,入赘苏州长洲县张声远家,所以文惠这一支一直生活在苏州城德庆桥西北的曹家巷。文定聪其他三子均生活在杭州。
定居苏州的文惠就是文徵明的曾祖父。文徵明的祖父文洪(1426—1499)是家中长子,在苏州以办私塾教书为生。成化元年(1465年),文洪四十岁,这一年他才考中举人,后来他又连续参加三次会试,不中,直到五十多岁才被吏部选派到涞水县任儒学教谕。干了四年,他便告老还乡。[14]
文洪育有三子一女。三个儿子全都接受了儒学启蒙教育和科举考试训练。长子文林于成化四年考中举人,成化八年考中进士,是苏州文家第一位进士。十五年之后,文洪次子文森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考中进士。三子文彬能武,善骑射,以年资贡礼部。唯一的女儿叫文玉清,少时也接受过家庭教育,“通孝经语孟及小学诸书”,即读过《孝经》《论语》《孟子》等书。
文徵明的父亲就是文林。文林娶妻祁守端,于成化五年(1469年)生下长子文奎(后改名为文徵静),又于成化六年生下次子文壁,也就是文徵明。
文林是一位目光敏锐的官员,待人厚道,处事正派,对中国道教文化很有研究,所以给儿子取的名字也都与天上的星宿相关。古人仰望星空,将黄道、赤道带附近的星象划分为二十八星宿,而“奎”和“壁”就是星宿的名称。我们现在熟知的“徵明”这个名字,原是他的字,他自四十二岁起渐以字行。
文徵明出生后一直不会说话,人们甚至怀疑他有智力障碍。但是,他的父亲认为这种现象是贵人讷言,需要耐心等待时日,必可晚成大器。文徵明的母亲是里中人,稍读诗书,还能够描绘几笔兰花闲草[15],在那个时代算是有文化的女性,对这个不会说话的“哑巴”次子,更是关怀备至。
文林于成化四年考中举人后,未能连中三元。隔了一届,到成化八年才在殿试中考取进士,名列第三甲,随后被任命为温州永嘉知县。文林一家四口带着两个仆人,一起赶往温州上任。那时,文奎四岁,文壁三岁。
文林在永嘉知县任上一共待了六年。其间,因为朝廷经常拖欠官员薪俸,一家人过得捉襟见肘,祁氏还曾变卖首饰,以维持家用。此时在涞水县担任教谕的父亲文洪,打算回苏州故里养老。文林是家中长子,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于是托付妻兄祁春将妻子和两个儿子一起送回老家苏州,提前为迎接老人回家做准备。
这是成化十二年春天的事。可是妻子祁守端回到苏州老宅突发急病,竟于当年五月二十七日撒手人寰,年仅三十二岁。文林悲痛难忍,邀请当时最负盛名的文人李东阳撰写了《文永嘉妻祁氏墓志铭》,足见他对妻子的厚意。
这个时候,苏州曹家巷的文家老宅已无长辈在家。文徵明的祖父文洪和继祖母以及两位叔叔尚在涞水,还未归来,因而八岁的文奎和七岁的文壁在生活上顿陷困顿。此时外祖母家施以援手,将这两个孩子接去了母亲祁氏在里中的娘家。但外祖母徐氏年老,做不了多少家务,母亲祁氏的妹妹祁守清给予了这两个苦命的孩子无私关爱。
小姨祁守清家贫,丈夫又新逝不久,自己还有幼子需要照料,可是她依然三天两头跑来娘家,照顾这两个小外甥,并将家里的旧衣服缝缝补补,给小外甥做成合体的衣裳,让孩子们感受到亲情和温暖。舅舅祁春是个辛苦奔波的小生意人,经常为孩子们送来粮食和衣物。文徵明长大后,对这一段艰难日子感念于心,念念不忘。外祖母徐氏、小姨祁守清以及舅舅祁春去世时,他们的墓志铭都是由文徵明饱含深情撰写。
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即成化十三年(1477年),发生了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八岁的文徵明终于能够开口说话了。
成化二十一年,文林升任南京太仆寺丞后便告假省亲,携家眷一起返回苏州故里。这时候,文林已经有了第三个儿子。除文奎、文壁之外,他又有了第三子文室——在原配祁氏去世后,文林在永嘉知县任上娶了吴氏为妻。吴氏为永康县(今永康市)教谕吴清的女儿,文室的生母。苏州文化圈对文林父子的归来,表示了热诚欢迎。他们经常雅聚,迎来送往,把酒举杯,畅叙诗怀。
也就是在这一年,唐伯虎与随父还乡的文徵明相识了——这时的唐伯虎初露锋芒,在与张灵等一起参加的苏州府童生试中取得佳绩。
令人诧异的是,唐伯虎与文徵明初相逢就成了挚友。是年,两人都是十六岁。
这种惊讶不无原因——两人性格反差极大。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唐伯虎整天跟张灵厮混在一起,性格由内向开始转为外向,常有不知天高地厚之举,令人侧目,而文徵明的性格正好与之相反,他待人谨慎,虚怀若谷,是刘嘉䋭那种人见人爱的标准好少年。文徵明生长在世代饱读诗书的家庭,自小就心悦诚服地接受儒家教育,而唐伯虎所接受的应试教育,则具有浓厚的“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功利色彩,与文徵明的情况完全不同。
看似性格相左、家庭背景迥异的两人,恰好形成了性格上的互补,像两块相互吸引的磁铁一样,文徵明和唐伯虎至此成了好友,而且这种真挚的友谊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需要指出的是,文徵明绝不是天才少年,甚至小时候给人的感觉是他很笨。但是,文徵明有个突出的优点,他兴趣广泛,学习十分勤勉。后来他又遍学名门——曾“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皆父友也”[16]。这些大名士都与文林友情深厚。当年文林考中进士外派为永嘉知县时,同榜状元吴宽写了题为《送文宗儒知永嘉》的送别诗:“同年出宰联翩去,大邑争夸浙水东。”所以当老友白璧微瑕的儿子文徵明前来求教学问时,他们都予以热情指导。
文徵明十六岁回到苏州不久后,就认识了都穆,并开始跟随他学诗。几乎每写一首,文徵明都要请都穆斧正,都穆也总是尽心竭力地辅导。文徵明回忆说:“余十六七时……余每一篇成,辄就君(都穆)是正,而君未尝不为余尽也。”[17]
在与唐伯虎订交后,因为父亲要赴任南京太仆寺丞(南京太仆寺的官衙在安徽滁州,距离南京不远),文徵明也跟着一起离开了苏州。到弘治元年(1488年),文徵明已经十九岁了,为了入县学读书,他才从滁州回到故乡苏州,顺利地进入长洲县县学成为生员。
到了当年年底,长洲县学按例举行了岁试,考试结果令文徵明感到震惊和羞愧:他仅仅被评为第三等。
按照科举教学的管理条例,每一届提学官在任三年,要在县学里举行两次岁试(岁考),用岁试成绩来甄别诸生的优劣,共分为六等:“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有缺,依次补充,其次补增广生。一、二等皆给赏。”廪膳生的待遇和老师一样,“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三等如常”,“不得应乡试”,“四等挞责”,“挞黜者仅百一,亦可绝无也”。[18]三等生及三等以下者均无法参加乡试,属于后进生。
文徵明的父亲是当朝进士、苏州名人,而他的儿子在县学的考试成绩居然快要垫底,这确实很伤自尊。文徵明忸怩了半天,还是不服气,就跑去问老师。“宗师批其字不佳,置三等。”[19]先生指出:成绩不佳的原因,就是他的字写得实在太差了!
文徵明没有与县学老师争辩,而是虚心接受批评。自此,他发愤练字,夜以继日,并且持之以恒。
诸生在县学里读书,本应每日起早贪黑,实际上他们“皆饮噱啸歌,壶弈消晷”,也就是大家趁老师不在的时候,偷偷喝酒、娱乐,以投壶游戏消磨时光。而只有文徵明一人坚持伏案习字,专心致志地临习智永的《千字文》,而且每天临习“十本为率,书遂大进”[20],终于练就了十分扎实的功底。
文徵明后来成为明代著名的书法大家之一,人们对他当初学书的途径极为关注,欲加以仿效。他的次子文嘉著文介绍说:“先君少以书法不及人,遂刻意临学。篆师李阳冰,隶法钟元常,草书兼抚诸体,而稍含晋度,小楷则本于《黄庭》《乐毅》,而温纯典雅,自成一家,虞、褚而下弗论也。”[21]他所指的就是这一时期。
此时,苏州最享盛名的大画家是沈周(1427—1509),他比唐伯虎与文徵明大了四十多岁,被推崇为整个明朝最伟大的画家。沈周与文家有亲戚关系,属于远亲。文林的表弟桑悦是苏州常熟人,也是他的会试同年。而沈周的夫人是常熟人陈慧庄,系陈原嗣之女、陈蒙之妹,正是桑悦的姑母。文徵明出生当年,文林就曾去拜访沈周,自此两家关系热络起来,彼此常有诗画相赠。文林与父亲文洪因故滞留徐州时,沈周还曾写诗《怀文宗儒父子久客徐州》,表达了自己的惦念之情。

◆明 文徵明 小楷书《千字文》,藏处不详
沈周是桑悦的姑父,桑悦又是文徵明的表叔,按辈分文徵明应该称沈周为爷爷。文徵明虽然自小热爱书画,但因其学习的重点是科举,又加上常年随父亲在外地生活,所以直到二十岁才成为沈周的入门弟子。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文徵明虽然不具备唐伯虎那般喷薄的才华,可他是一位特别有教养的少年,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且成了笨鸟先飞、勤能补拙的典范。
我们从他的经历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徵明九岁即跟随其父的科举同年、当时已是一流大家的吴宽学写文章;十六岁跟随都穆学写诗;十九岁又跟随祝允明的岳父、书法名家李应祯学习书法;二十岁追随沈周学习绘画。他如同海绵一样汲取知识,以增强自身的文化涵养与能量。
而在与唐伯虎的交往中,文徵明始终为人低调,处处谦虚谨慎,克制自己,所以二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实际上,低调是一种精神境界,越是饱学之士,越是自觉学识欠缺,不高调,不张扬。
[1][明]杨循吉:《松筹堂集》卷六《明故刘文学墓志铭》。
[2]同上。正统九年,刘昌乡试第一,后会试第二,中进士。景泰二年授南京工部主事。历官河南提学副使,迁广东左参政。
[3]《六如居士全集》卷六《刘秀才墓志》。
[4][明]王穉登:《吴郡丹青志·张灵》。
[5]《新倩籍·张灵小传》曰,张灵“家本贫窭,而复佻达自恣,不修方隅,不为乡党所礼”。
[6]《新倩籍·张灵小传》:“惟祝允明嘉其才,因受业门下。”
[7][明]黄鲁曾:《续吴中往哲记》卷一。
[8]《续吴中往哲记》卷一。
[9][明]李绍文编撰:《皇明世说新语》卷六《任诞》。
[10][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九十一。
[11][明]曹臣:《舌华录·冷语第六》。
[12]《吴郡丹青志·张灵》
[13][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
[14]周文翰:《文徵明传》,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1页。
[15]据《苏州府志》记载,成化年间,祁守端在永嘉令署作花卉图。
[16]《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三》。
[17][明]文徵明:《南濠居士诗话序》。
[18]见《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
[19]潘承厚辑:《明清画苑尺牍·文徵仲》,转录自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中华书局,2020年,第40页。
[20][明]何乔远:《名山藏·高道记》,转引自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第44页。
[21]见日本东京堂本《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六卷,文嘉跋《文徵明四体千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