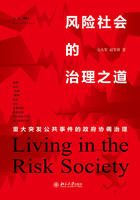
二、何为协调
从语义角度讲,协调与“协”“调”同义。在《辞海》中,“协”有和、合,帮助、和谐、协调之意;“调”则被理解为协调、调和。[1]在《辞源》中,除清代军制名称外,“协”被认为有三层含义:①和,即和睦、合作的意思;②服从;③相同,相合。“调”也被认为具有三种主要的意思:①调和,调节;②畜养、训练;③嘲笑,调戏。[2]可见,在对“协”与“调”的理解中,实则包含了两个层面的认识:一为事物之间的和合关系与状态,属静态结果层面;一为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行为,属动态过程层面。在西方,英语中的“harmony”“harmonize”“harmonious”即协调,它们源自希腊语“harmonia”,同样包含和睦、融洽、一致以及调和之意。总之,从语义上讲,“协调”是指正确处理各种关系,使关系处于一种和谐状态。
在不同的学科视野中,“协调”的内涵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协调”作为专业术语使用始自近代的管理科学,“协调”的语义更多的来自企业管理。在企业管理研究领域,法约尔(H.Fayol)较早地指出了“协调”的重要性。法约尔认为,协调与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在管理中具有同等的地位,是管理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和基本要素之一,它能将不同的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在1916年出版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法约尔认为,协调就是“连接、联合、调和所有的活动及力量”,“让事情和行动都有合适的比例,就是方法适应于目的”[3]。古利克(L.H.Gulick)的管理“七职能论”同样包括了协调,他指出,组织理论必须探讨协调结构问题,企业中进行分工的单位都要加强协调工作。从管理学对协调的论述看,组织管理活动中的协调离不开组织内部的分工,即部门的分设,它是管理活动有效的重要纽带,对组织目标的达成具有重要的工具价值。詹姆斯·G.马奇(James G.March)和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Simon)则突破了协调是管理基本职能的分析框架,认为协调就是对任务和资源进行划分并在组织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的基本组织活动过程。[4]詹姆斯·D.汤普森(James D.Thompson)提出了组织协调问题产生原因包含的三种基本依赖关系:总和关系、顺序关系和互动关系。[5]
在协调被作为组织体系内部活动特征来看待而受到关注的同时,系统科学的视角也受到了重视。在国内,王维国是比较早地对协调进行定义的学者。他认为:“既不能离开系统的演化来讨论协调,把协调当成结构稳定的同义语,也不能把协调等同于平衡,把协调范畴仅仅归结为系统结构的静态比例关系。协调应是发展的一种规定,是对系统的各种因素和属性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程度的反映。”[6]基于此,他提出,“协调是指为实现系统总体演进的目标,各子系统或各元素之间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而形成的一种良性循环态势”[7],进而指出了理解协调应当包括的几个方面:目标、因素、关系、协调性和动态性。
熊德平在结合管理学和系统科学的基础上提出,协调是指在尊重客观规律,把握系统相互关系原理的基础上,为实现系统演进的总体目标,通过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方法和力量,依靠科学的组织和管理,使系统间的相互关系达成理想状态的过程。[8]熊德平进而指出理解协调包含的五大要点:其一,“理想状态”的判断和把握。“理想状态”是指为实现系统总体演进目标,各子系统或各元素之间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而形成的一种良性循环态势。因此,协调首先是一种关系,但又不仅仅是关系,关系是协调的前提和基础,协调只是协调的理想状态和实现过程。其二,协调以实现总体演进目标为目的,总体演进目标是协调的前提。其三,协调对象是相互关联的系统,协调是系统内外联动的整体概念,孤立的事物或系统组成要素不存在协调,系统间的有机联系是协调的基础。其四,协调必须有协调主体、手段、机制与模式。协调手段有自然的和人为的以及二者在不同程度上相互配合形成的不同形式。其五,协调是动态和相对的,是始终与发展相联系的具有时间、空间约束的概念。“理想状态”意义上“协调”的终极含义,决定了“过程”意义上的“协调”永无终极。
与企业管理研究中将协调作为企业管理的主要元素不同,在行政学领域,协调的地位则要低微得多。出于对政治与行政二分后带来的行政极易脱离政治的担忧,行政学的重要奠基人古德诺(F.J.Goodnow)认为,实际政治的需要要求国家意志的表达与执行之间协调一致,“法律与执行法律之间缺乏协调就会导致政治的瘫痪”[9]。在他看来,为了保证国家意志能够得到真正执行,“政治必须对行政有一定的控制”[10]。事实上,这种协调不仅体现在政治与行政之间,在政府体制中,协调同样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把每一种功能分派给一个分立的机构去行使是不可能的”,“在各政府机构领地的交界地区都存在着‘公地’”。[11]对于协调方式,古德诺指出,它“既可能存在于法定的正式政府体制之内,也可能存在于这种体制之外,而存在于政党之内”[12]。古德诺对行政协调思想的贡献还在于,他强调了协调所需的必要控制必须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不能随意僭越,否则会妨碍行政功能的有效行使,致使“国家意志执行中的普遍的行政效率以及人民表达国家意志的能力都将不可避免地大大降低”[13],进而使其失去存在的理由。某种程度上,古德诺的开创性研究奠定了行政协调两大研究路径的基础。这两大研究路径包括:其一为政策研究路径,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之间的协调,该研究路径在政策学中得到了广泛的探讨;其二为组织结构的研究路径,即组织机构各组成要素的协调,它既包括组织内部各要素的协调,也包括组织体之间的协调。随着政策学从行政学母体中分离,组织结构的研究路径逐渐成为行政学学科体系中行政协调研究的主要切入点。唐斯(Anthony Downs)从组织结构的角度提出,“任何组织的最初形成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如果不对从事不同任务的许多个体的工作进行协调,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意味着组织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愿意调整自己的行为与其他成员的行为相互协调”[14]。美国学者费斯勒(James W.Fesler)和凯特尔(Donald F.Kettl)在合著的《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中,对于协调的阐述更是直接置于组织问题的讨论中。我国的行政管理学者一般将协调看作一种活动或行为。夏书章、王乐夫认为行政协调是指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协调,是行政主体为达到一定行政目标而引导行政组织、部门、人员间建立良好协作与配合关系,以实现共同目标的行为。[15]张紧跟认为,协调是指在管理过程中引导组织之间、人员之间建立相互协作和主动配合的良好关系,以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实现共同预期目标的活动。[16]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协调的内涵可以从三个角度得到:从组织关系的角度,协调表现为一种工作方式;从结果的角度,协调表现为一种组织的整体和谐状态;从过程的角度,协调表现为一种规范化行为。[17]
通过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梳理对于协调的界定可以发现,一般意义上的协调包括三重内涵:协调是一种缓解冲突、消弭分歧、引致合作的行为;协调是同一系统、同质系统和异质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协调规定了不同主体或者不同系统之间的权责边界,协调会引致治理。
[1] 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488页。
[2] 参见《辞源》,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17、2905页。
[3] [法]H.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周安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115页。
[4] See J.G.March & H.A.Simon,Organizations,John Wiley & Sons,Inc.,1958.
[5] See Thompson,Organizations in Action,McGraw-Hill,1967.转引自郑冬艳:《基于网络的组织协调若干问题研究》,天津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6] 王维国:《协调发展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东北财经大学1998年博士论文。
[7] 同上。
[8] 参见熊德平:《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9] [美]F.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王元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10] 同上书,第15页。
[11] 同上书,第8、9页。
[12] 同上书,第21页。
[13] 同上书,第25页。
[14] [美]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郭小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15] 参见夏书章主编:《行政管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289页。
[16] 参见张紧跟:《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17] 参见史瑞丽:《行政协调刍议》,载《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