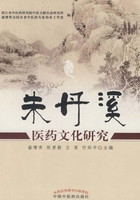
朱丹溪气血论治的探讨
气血论治是丹溪学术的重要组成,是其“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治疗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对东垣学术思想的深入发挥。
(一)气血论治的指导思想
丹溪师事罗太无,印象最深有两件事:从一病僧治疗过程中,“大悟攻击之法,必其人充实,禀质本壮,乃可行也;否则邪去而正气伤,小病必重,重病必死”;二是见罗太无治病并无一定之方,“大悟古方治今病,焉能吻合”?这两个大彻大悟深刻地影响了丹溪的治疗观,一则重视正气,奠定气血论治的思想基础;二则主张辨证用药,不拘成方,成为《局方发挥》的基调。丹溪以东垣思想为指导总结罗太无经验,完善了自己的治疗思想: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
保护正气的思想基础在于对疾病发生机理和药物性能的认识,虚证属精气之虚,必须扶正固不待言,即使邪实证的根本原因仍责其虚。“夫邪所客,必因正气之虚,然后邪得而客之,苟正气实,邪无自入之理”。正气主要指气血而言,“人身所有者,血与气耳”;“血气者,身之神也,神即衰乏,邪因而入,理或有之”,因此,这种治疗思想指导下的气血论治,其特点偏于补虚,所以丹溪孜孜于补气养血之治,多从气血不足的角度考虑问题。丹溪私淑弟子王纶所谓气血论治主以四君、四物,正是补气养血的代表方,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丹溪这一特点。
(二)气血辨证论治
《格致余论》讨论病证十八种,其中八证从虚立论;《金匮钩玄》责病因、病机之虚有79门之多,占了56.9%。从虚认病识证,体现了护正观点,这是丹溪一大特色。疟疾的发病特点是“弱质得深病”,胃气之伤是病变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治虽当汗解,却须参术之补以助汗,不可劫药以求速效;神志错乱当责虚病、痰病,总由“气血两亏,痰客中焦,妨碍升降,不得动用”,方药主张用补脾益气、清热导痰,补益居祛邪之先。妇科诸疾尤重气血,难产之由责之气虚不运,“补其母之气,则儿健而易产”,立大达生散一方,参术归芍草补其气血之虚,紫苏、陈皮、大腹皮以行气滞;“难产之后,血气尤虚”,其治胞损淋沥,即以峻补成功。孕妇转胞由于“血少则胞弱不能自举”,治用四物加参术二陈之类;不孕“率由血少不足以摄精”,“欲得子者,必须补其阴血,使无亏欠,乃可推其有余,以成胎孕”。堕胎或由内火之动,或由血气虚损,所谓白术、黄芩乃安胎圣药,正是从这两方面着眼的。经水紫黑当责血热,然血为气之配,故“见有成块者,气之凝也;将行而痛者,气之滞也;来后作痛者,气血俱虚也;色淡者亦虚也……”。痈疽若发于多气少血之经,不可遽用驱毒伤血之利药,可用大料人参。《格致余论》从气血俱虚立论八证,涉及内、外、妇各科,很能反映丹溪的治疗特点。
气血实证从热从郁,但仍不忘顾及其虚。鼓胀病起于阴阳失调,气化浊,血瘀郁而为热,湿热熏蒸而成胀满,根本原因却在脾土受伤,治宜补脾为先,所附医案均以补气养血获安,所谓“知王道者能治此病”。呃逆属木邪夹相火上冲的气逆实证,本在土败木贼,泻火当兼扶土,诸案俱责其实,药用大补丸、益元散,仍以人参白术汤下,取吐则用参芦,可见其意所在。
(三)补气养血方法
“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王纶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丹溪气血论治重视补虚的理法方药特点。
四物汤是养血补血主方,见于《金匮钩玄》有二十九门,其中明言血虚无血的有十四门,阴虚五门,混言虚而不分气血二门,病后调理二门,血虚血热共用三门,合计二十六门从虚着眼。另有呕血、脚气、酒糟鼻三门责之血热。此外尚有用四物之药而不出其名的,如头风“属血虚,川芎、当归、芍药”;血虚头痛,“必用川芎当归汤”;痛风“多用川芎、当归,佐以桃仁、红花”;痢疾亡血,“倍用归身尾,却以生芍药、生地黄、桃仁佐之,复以陈皮和之”。诸方实属四物化裁,合而计之,全书用四物就有三十三门之多了。至于血虚而不用四物的,惊悸“主血虚,用朱砂安神丸”;痉“多是血虚有火兼痰,人参、竹沥之类”;产前胎动血虚用阿胶,仅此三门,可见丹溪补血用方之专。
东垣补气健脾的特点是升阳燥湿,喜用辛温升散的风药,丹溪认为“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故补气多兼血药的阴柔滋润而不取风药的升浮温燥。《金匮钩玄》气虚诸门用升柴的,伤寒须发散外,即水肿、泄、浊、脱肛、小便不通、血崩等,俱为下焦病,可见丹溪掌握这类药物适应证的严格了。同样的道理,丹溪认为茯苓是“暴新病之要药也,若阴虚者恐未为相宜”,虽利湿化痰常用,由于不符合滋润阴柔的用药特点,一般的补气方中就少选用,这也影响了四君子汤的运用。《金匮钩玄》断为气虚三十七门,三十门有方药,四君子汤仅五见;而二十一门只出药不名方,人参、白术最多用,而回避了茯苓,即可明其中奥妙。所谓“气用四君子汤”,实未深究丹溪旨趣。
当然,丹溪注重气血并不主张一味蛮补。所谓“诸痛不可用人参,盖人参补气,气旺不通而痛愈甚矣”,即是其例。
笔者统计分析了《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所载344则丹溪医案,其中指出病机169则,有血虚19则,气虚16则,不分气血27则,阴虚阳虚各5则(其中属气虚血虚6则),共有气血虚68则,占40.2%;所有319则出方药的医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药物是甘草、白术、人参、陈皮、当归、芍药、茯苓、川芎,除陈皮外,全是补气养血药,212则使用成方的医案,四物44则,四君仅6则,其他补气血方17则。病机认识和运方用药规律基本一致,客观地反映了丹溪重正气重气血的治疗观点。
(四)气血论治与阳有余阴不足相火二论
阳有余阴不足论是谨身节欲的养生论,阴指生殖物质,又与全身气血不可分割。气血是生殖物质的源泉,《色欲箴》说:气阳血阴,人身之神,阴平阳秘,我体长春,血气几何,而不自惜?情欲伤阴,损耗生殖物质,归根结底仍要戕伤气血。《阳有余阴不足论》开宗明义就提出气血的有余不足及其随月盈亏而消长进退的看法,原因亦即在此。《相火论》倡言相火元气之贼,认为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以真阴、元气相提并论,申明火热损耗气血真阴的病机特点。因此,丹溪主张清泻妄动之火使不伤阴耗气,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保护气血的观点。丹溪所说的泻火为补阴之功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气血论治与相火论,一从正气着眼,一从邪气立论,从不同侧面体现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对邪正双方的观察分析,虽各有侧重,终究有着密切联系。两相结合,对疾病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刻,施治也更为准确周到了。
(五)气血论治到养阴学说的发展演变
丹溪气血论治注重脾胃生化之源,具有甘温濡润的用药特点,这一宝贵的学术思想、实践经验和用药风格,为后世养阴学说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和经验。王纶注意到丹溪用药滋润阴柔的特点不同于东垣,从阴阳对立出发,认为丹溪主用血药补血而东垣气药补气,气虚之与血虚如冰炭相反,而阴、血性质上的共性,使他把气血论治发展到养阴学说。王纶认为阳有余阴不足就是精血既亏,相火必旺,用四物加黄柏、知母补其阴而火自降,此用血药以补血之不足者也,进而由补血引申为滋阴,常补其阴,使阴与阳齐,则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斯无病矣。故丹溪先生发明补阴之说,谓专补左尺肾水也。在这个理论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滋水降火的治疗法则和补阴丸方,首次把滋阴理论和方药直接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成为养阴学说的嚆矢。薛己在《明医杂著》的基础上提出真阴真阳说,赵献可、张景岳进而完成滋阴说。溯其源,可见丹溪气血论治的理论价值。
(刘时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