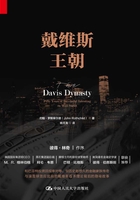
只有股票才是超级财富的创造者
戴维斯家族在1941年成为纽交所席位的拥有者,在1945年成为房产拥有者。1945年,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战士们胜利回国,股市中的战争行情渐渐接近尾声。这个时期,即便股市有所恢复,道琼斯指数以及其他主要指数依然低于1929年的行情。潜在投资者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们心中怀有大萧条会再次来临的恐惧,担忧高高在上的分红税率(当时的资本利得税率倒是相对合适,但在这样糟糕的市况中,谁有资本利得呢?)。他们也认为和平对于经济的发展并非好消息。一些人甚至预期下降的出生率会破坏未来的繁荣(这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一个观点)。大多数人继续迷恋20世纪30年代的资产赢家:债券。
戴维斯没有追随大众的这股热情。尽管债券在过去的十年是赢家,但他意识到只有股票才是超级财富的创造者。股票是一个企业所有权的一部分,如果这家公司能兴旺发达,那么股票应该可以说是具有无限的上升空间。一个债券持有者的所得只不过是本金的返还加上一点利息,无论发债公司如何优良,与债券持有者毫无关系。
更有甚者,尽管政府依靠发行国债筹集资金,开展各种活动,但历史显示,各种类型的政权都会将忠实的债券持有人拖入通胀的泥潭,特别是在重大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战争的努力虽然令美国工业重新焕发生机,但代价也是惊人的,开销远远超出最为疯狂的想象。1943年,美国政府的花费是惊人的720亿美元,超出预算160亿美元。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公司总市值也仅有360亿美元,也就是说,联邦政府一年的开支超出美国上市公司全明星阵容总市值1倍。
这就存在一个可预见的麻烦:政府缺乏资金来支持战时费用无节制的狂欢。政府只能通过老办法解决这类问题:提高税收、发售债券、在联邦印刷机上印发钞票。这是经典的应对策略:以廉价的货币偿还战争债务,尽管廉价的货币会引发通货膨胀。为了平息投资者的怨气,美国财政部采取一种笨拙的方式,会给发行的债券扣上一个利率的“帽子”。只要利率不上升,债券的价格就不会下跌。这样,债券投资者就可以暂时免于价格损失的打击,不至于损害他们对于债券的热情。
但是,暂时终归是暂时的。那些购买山姆大叔债券的投资者实际上是三重打击的受害者:(1)扣在利率上的“帽子”剥夺了他们应有的公平市场回报。(2)由政府印钞引发的通货膨胀侵蚀了他们本金的价值。(3)在所得税方面,投资人获得债券收入的最高税阶征税率达到94%。与此同时,无所不在的广告大肆宣传购买债券是爱国行为,而盲目顺从的爱国行为让人购买政府印发的任何债券。
一般的投资者通常买不起以10万美元为单位的债券,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将他们的钱存在当地银行或储贷社的账户里。这些钱受到新成立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保护。各类存款机构支付给储户的利率非常低,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对此,储户们似乎也不太看重,他们更关心的是保住本金,而不是取得更多收益。
这三重打击的最大受害者是那些富裕人士以及各类机构(退休基金、保险公司等同类机构)。这些经验老到的投资人本应该看得出在20世纪40年代持有政府债券是愚蠢行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做出明智之选。对于债券牛市的结束,他们各抒己见,充满臆想。他们认为,因为债券在过去十年利润丰厚,所以,它们在未来依然会继续给投资人带来厚利。他们相信联邦政府肯定会阻止利率的上升,因为政府连猪排的价格都会控制,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当然也会控制贷款利率。
此外,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通货膨胀在重返和平之后不是已经平息了吗?如此说来,那些笃信“历史会一再重演”的商学院学术派专家预测,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通货膨胀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消退。此外,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紧缩更是引发了人们对于通货紧缩再次降临的担心。
戴维斯对这些担心和预测并不理会,他成了一个反债券的特立独行者。刚刚经历了债券投资的既吸引又安全的旅程,人们面对的现实是,按照戴维斯的说法,债券是丑陋并且危险的。很快,利率已经跌到了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的“清汤寡水”的地步,凯恩斯的这个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很有道理,长期的国债利率已经跌到了谷底,到1946年4月利率跌至2.03%。这些债券的买家需要等上25年才能将他们的本金翻一番,在戴维斯看来,这样的复利实在是太可怜了。他看到一种威胁的存在,“美国国债的金钱海洋之上,漂浮着最为昂贵的战争代价”[1]。政府深陷债务的泥潭,迫于无奈,再次借了700亿美元的新债以缓解当时的财政短缺。戴维斯断定市场上的出资者很快会要求更高的利率,而不是更低。1946年,用于测量通货膨胀最为可靠的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迅速上升。债券的牛市对于通胀的爆发置若罔闻,视若无睹,全然忘记了一个基本的投资常识:当CPI上升时,回避债券。从中引发的第二个教训是:在一场昂贵的战争之后,回避债券。在戴维斯看来,藏于政府发行债券中的富矿时代过去了。
戴维斯将他在纽约州保险司的岗位变成了一个演讲台。过去的十年中,很多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常常用天堂般安全的债券来填满它们的投资组合。现在,考虑到债券市场的高风险、低回报,他建议保险业精英减少他们的债券持有数量,投资更多的房地产、按揭或股票。无论是亲自出马,还是以书面形式,他都不遗余力地反对那些对股票的偏见,反对那些对债券持有非理性繁荣观点的谬论。1945年7月,他给《分析师期刊》撰写文章,指出:
在过去的四年中,很多寿险公司非但没有打破债券的束缚,反而被爱国的狂热卷入得更深,在债券市场的参与度达到空前水平……对于他们而言,更为健康的发展,应该是以多元化的形式参与到美国经济中,就像他们之前做的那样。
对于部分由监管引起的问题,戴维斯努力推动监管规则的转变。在一些州,包括纽约州在内,当时的法规规定,保险公司持有任何股票均为违法行为。即便在稍微宽容的州,也仅仅允许保险公司持有少量的股票。经历了1929年大崩溃的磨难以及之后的余波不断,保险公司的管理层对于股票的恐惧与厌恶,已经使他们对股票的态度与监管层并无二致。1941年,在一次著名的听证会上,美国大都会保险公司的总裁弗雷德里克·埃克指责,股票是大萧条期间纽约外围60家保险公司倒闭的罪魁祸首。埃克说,纽约州没有一家保险公司倒闭,这个事实说明了纽约州对股票说“NO”的策略是明智的。
对于戴维斯这种反潮流的举动(支持股票、反对债券),支持者甚少。在家庭内部,凯瑟琳的哥哥积极主张在沃瑟曼家族信托中增加持有股票的比例,他赞同戴维斯的主张,认为国债以及政府发行的其他债券简直就是一张“财产没收证明”。在政界和商界,罗斯福总统的杰出顾问萨姆纳·派克赞同这个观点,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公平人寿保险公司的总裁托马斯·帕金森。为人直爽的帕金森经营公平人寿保险公司已有25年之久,他痛斥同行对于政府过度印钞保持沉默的态度。“这个国家,”帕金森说,“已经被失去控制的国债利用,在美联储系统体面的外衣之外,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虚拟货币。”
帕金森和其他一些铤而走险的保险业大亨一起,在当时那些面上无光的公用事业公司和陷入困境的铁路公司发行的垃圾债券中,寻求更高回报的标的。然而,更甜美的回报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多代价,最为极端的情况,是这些“体弱摇晃”的公司会债务违约,还不起钱。当时,这样的情况很多。垃圾债券的违约给保险公司持有的投资组合造成很大损失。
“至少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人寿保险行业的投资所得少于它们承诺给予客户的回报。”戴维斯如此评价。长此以往,保险行业必将破产。
注释
[1]Shelby Cullom Davis,America Faces the Forties,Dorrance&Company,1940.